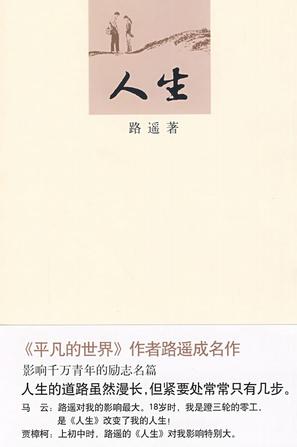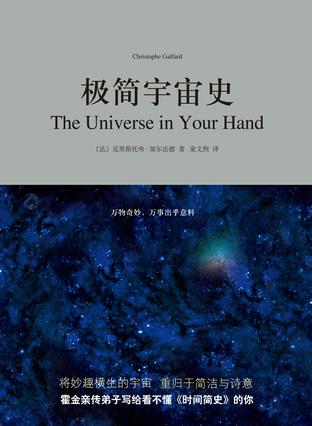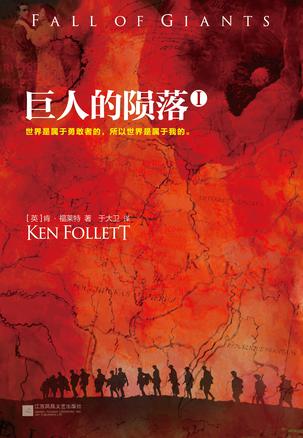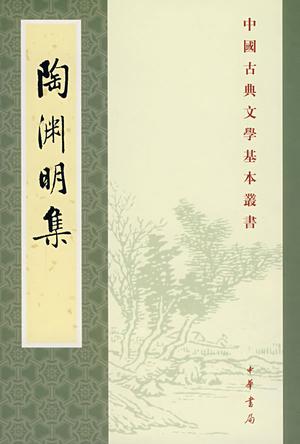-
中原(慎一郎):最近,我把自己不懂但有兴趣的事物叫做“Gray”(灰色)。例如,我会这么说:“我对这段谈话很感兴趣,但对我来说它是灰色的。”然后将它保留在心里,(笑)
-
有一天,我猛然下决心去寻找您。我情绪低落到极点。须知局势恶化,令人担忧,山雨欲来风满楼,大祸将至。我们生活在一个“奇特的时期”。无所依托。于是我想起还有个父亲。当然,我经常想到“乔治五世地铁车站的痛心事件”,但我对您并无丝毫怨恨。对有些人,什么都可以原谅。十年过去了。您的情况如何?也许您需要我。
-
迪迪并非真正地活着,而只是有一条生命。这两者不是一回事。有些人就是自己生命的本身。还有些人,比如迪迪,只是栖身于生命之中。他们就像没有安全感的房客,总是不清楚哪些东西是自己的财产或租约什么时候到期。或者像拙劣的绘图员,为某个异国他乡一遍遍地描绘着错误百出的地图。 对这种人而言,到头来注定一切都会耗尽。
-
无论同一性是以什么方式被构想的,它的优先地位都界定了表象的世界(monde de la représentacion)。而现代思想却诞生自表象的破产,同一性的破灭,以及所有在同一之物的表象下发挥作用的力(force)。现代世界是拟向(simulacres)的世界。在拟象的世界中,人不会在上帝死后幸存,主体的同一性不会在实体的同一性死后幸存。
-
我非常喜欢这种毫无意义的所谓交流,我们净说一些俏皮话,在这里虚晃一枪,在那里做一个谜一样的暗示。我对目前毫无意义和毫无价值的生活还不满足,还需要更多无意义的东西。
-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可怕的思想在折磨着我:只有我们夫妻俩的生活才过得这样糟,而不是像我从前所期望的那样,在别的夫妻的生活中是决不会有这种情形的。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共同的命运,但是大家也都像我一样认为,这是他们特有的不幸,于是也就把自己的这种特有的、觉得羞于讲出口的不幸掩盖起来,不仅不让别人知道,甚至也不让自己知道,自己对自己都不承认这一点。
-
我认为言论自由是其他所有形式的自由的前提。如果言论自由消失了,那么其他所有的自由形式就会受到威胁。限制言论自由是当权者的武器,他们以此来杜绝批评的声音,再进一步控制人们的行为。社会用来抵抗权力滥用的唯一防御性武器就是言论自由。这种自由是其他形式的自由得以存在的前提保障。
-
“人···…具有不用根就与土地相连的特性” (爱比克泰德,谈话,Ⅲ,24,9)。
-
这种蔓延的温情,就像本源一样,是被遴选的假想,它不断提醒人们去把握它,让这个想象招人喜爱,变得有人情味,成为文化现实。那么这个回到乡土,用现代情感改造《奥德赛》的最佳方式,也许并不是你的方式吧? 故乡就像一种语言,“没有归属”。
-
在这里,我和各个年龄段、来自各行业的人打成一片——在这种小地方也只能如此——而在伦敦我却只是沧海一粟。当年选择去大城市,是因为我想认识不同的人,开阔眼界,扩大社交圈,但最终我只是和一帮与我极其相似的人泡在了一起。因而我能获得经验和阅历越来越少、越来越狭窄,再也不可能遇到什么新人新事,我们都厌倦了这样的生活。
-
伦敦这个地方,就是让你来挑战自己的。那些在家乡获得省级迪斯科大赛冠军的家伙,或是在学校里出类拔萃的天才学生,一到此地就变得什么也不是了。然而,在这儿无论如何也能收获些精彩——比如实习的机会,或不错的周末派对,所以他们还是决定到伦敦来闯一闯。我们都是为了成功和成功所带来的欢喜,不惜与“不稳定”和“竞争者众多”作斗争的人。
-
“每个人都在追求法律,”男子说,“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除了我再没有别人要求进入这道大门呢?”守卫看出男子的生命已到尽头,为了男子那渐渐消失的听觉还能听清楚,守卫对他咆哮道:“别人也进不去,因为这道门仅仅为你而开。现在我要关上门离开了。”
-
他在这不能自制的愤怒时刻,把所有一切都一股脑儿哭了出来:信任、热爱、虔诚、尊敬——他的整个童年。
-
她像许多人一样,一种自认为优于他人的情感,在处于狼狈境地时,常用一种粗暴的方式来救助自己。
-
他们安静的忍耐让非人的生存环境、让低廉到践踏人的尊严的工资合理了。世上竟有这样的生命,靠着一小罐米饭一撮盐活下去。
num676-690
共85733
相关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