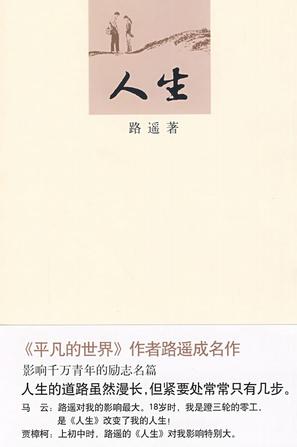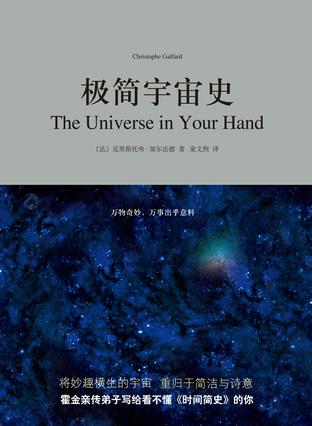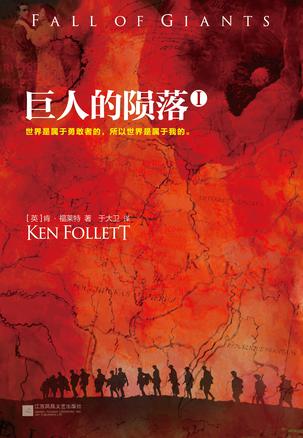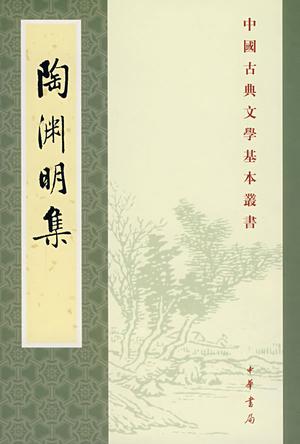-
琉璃厂是北京一条古老的文化街。自清代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全国文人聚集北京,这里开始兴盛起来
-
宋窑多青器,今人一见青器,即目为龙泉,误矣。柴、汝、官、哥,董色皆青,但有浓淡之分耳。柴窑吾不得见,官、哥、汝,余皆有藏品。釉水鲜艳,莫过官窑;匀润数汝,莹澈数哥;龙泉鲜艳不及官,匀润不及汝,莹澈不及哥,惟土细质厚,不易茅蔑,传世尚多。章生二有粉青器,用白土造,外加釉水,浅翠露白,精致绝伦,不以龙泉名,别称章窑。
-
接下来的3年,我肩负院长工作。有一天,我的上司(不过是副校长)狡黠地笑着对我说:“蒂姆,现在你是管理者了,是我们的一员。”我不寒而栗,想起了那本被搁置的《4A》。还会不会回到那些A那儿,或者自己已经不可挽回地穿越到了“另一边”?
-
就是这样,工作就是这么回事。大家都是出卖自尊在工作。工薪阶层不也是抹杀自己在上司面前卑微地附和着吗,这同我舍弃了自己的喜好和自尊心,来迎合慰藉那些下流的大叔们不是一回事吗?不能因为涉及了“性”,就非要扯上大篇幅的伦理道德,而让我的作受不必要的非议吧。
-
我理想中的推理小说,应该是“从第一页的第一行起到最后一页的所有叙述都是伏笔,最后一行阐明所有真相”。
-
他写了一部女性主义心理惊悚题材的作品,犀利地刻画了人心的阴暗面……
-
……然而硬皮的精装书、普通的软装书和小开本的文库本乱七八糟地排在一起,完全看不出他有心整理过。现如今,即使是偏远地区的旧书店,都不会把书塞成这副德行。要是有爱书人士造访,绝对会因这番惨状而气昏过去。 面对此般光景,确实没人能有心情在地上铺好被褥,美美入睡。
-
明代赐服纹样最高级别为蟒,其次是飞鱼。飞鱼由古印度神话中的摩羯演变而来,其头部似龙,两足(四爪),带双翼,鱼尾,并有腹鳍一对。后来又出现蟒形飞鱼,外形与蟒非常相似,四足,无翼,仅尾部保留鱼尾的特征。《明实录》中多见以飞鱼服赏赐镇边将帅的记载。
-
斗牛是次于飞鱼的赐服纹样。明代斗牛为蟒形,鱼尾,头上双角向下弯曲如牛角状。明代容像和服饰、织物上可以见到很多斗牛的形象。图中参考衍圣公府所藏深青色暗花罗缀绣斗牛纹方补单袍绘制。
-
在后唐马缟所著的《中华古今注》中有这样的记载:“秦始皇好神仙,常令宫人梳仙髻,帖五色花子,画为云凤虎飞升。”秦始皇热衷神仙之术,灭六国后第二年遇到方士徐福,两次派徐福出海寻求“仙药”,因此,其令宫妃打扮成想象中的神仙模样也很自然。
-
“勺”就是在脸颊处点红点,最初是宫中嫔妃作为标记使用,类似于戒指的功能。即颊有红点表示该女子处于孕期或经期,不便行夫妻之事,女史见之便不列其名。其原本只是宫闱内里之事,后来人们觉得妆容之中如此点缀楚楚可怜,有益姿容,此妆饰便在民间广泛流行开来,并在接下来的魏晋、盛唐达到流行的鼎盛。
-
Economic rationality has no room for authentically free time which neither produces nor consumes commercial wealth. – André Gorz
-
阴茎嫉妒(penis envy)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女孩在性心理发展期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因为自己与男性在生理上的差异而产生委屈、自电,甚至嫉炉的心理。这种“嫉妒”不仅是对生理特征的羡慕,更暗示着对权力社会地位的渴望,该建论为这种感受会影响女性的性格形成及其成年后的关系模式等。现今也会用于因自身生理构造产生自卑的男孩身上。
-
我开始在学生、朋友,甚至超市装袋工们的身上发现在病例分析会上所看到的那些微小但疯狂的苗头,然后我开始担心我看到的比实际要多。我开始着迷精神科医生们所看到的东西,好奇他们是如何知道他们所知道的东西的,以及他们是否是正确的,而这些又意味着什么。
-
我试过玩失踪,试过装疯卖傻,试过忘掉这一切。但是最终我明白了:人可以麻痹自己的良心,但却永远杀不死它。
num286-300
共89701
相关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