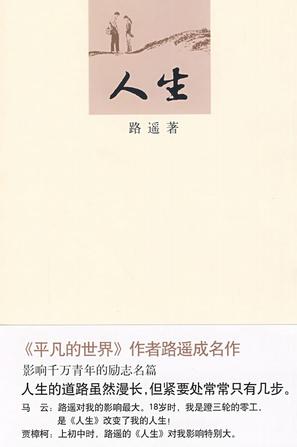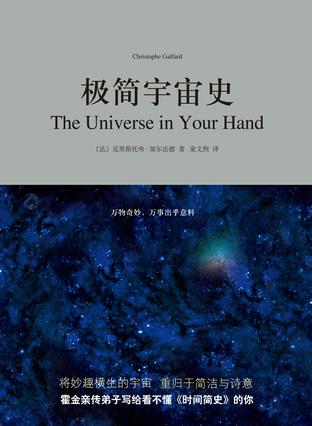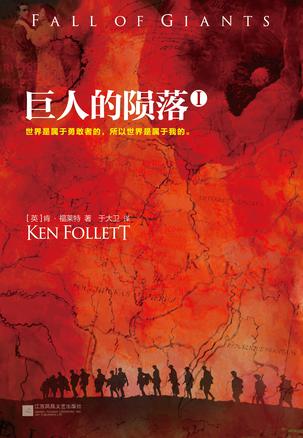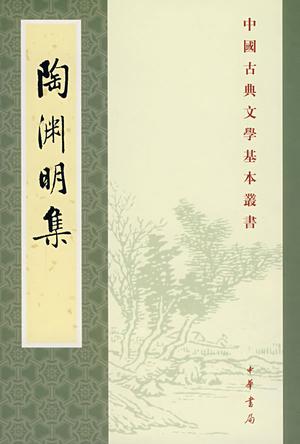夏日终曲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
-
好书网为大家整理了经典好书《夏日终曲》中的经典语录,精彩段落及优美句子,重读经典,感悟人生。让读者沉浸在自己的阅读世界里,忘记周围的世界, 与作者一起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快乐、悲伤、愤怒、平和,欢迎大家阅读~

我曾经担心该怎么宽衣解带;如果他不帮忙,我该如何像电影中的女人一样,脱掉我的衬衫,卸除我的裤子,赤裸裸垂着双臂呆站着,向他示意:这就是我,我就是这副德行,来吧,占有我,我是你的。
我多么喜欢他这样取笑我啊。
“所以。”我重复道,仿佛在谈及一个爱小题大做的第三者那反复无常的痛苦和悲哀,只是这个第三者恰巧是我。
其中的对比让他们很惊讶,大家唱了起来,尽管声音并不和谐,因为每个人唱的都是他们各自所了解的意大利小歌谣。
“你太聪明,不可能不了解,你们之间所拥有的情谊,是多么稀有、多么特别。”
不知何故,我边说,边努力做出讥讽和言不由衷的样子。
如果有一天,你想跟我聊聊,却觉得门是关上的,或者不够敞开,那我将是一个糟糕的父亲。
“我还要大波浪。还有布面草底凉鞋。还有太阳眼镜。还有你。”
接着我这样说道:“真相就是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毫无所感。如果我要见你的家人,我宁可不要有任何感觉。”接着是突如其来的沉默。“或许我们之间的事一直没有过去。”
但我也知道,预期最坏的状况,不失为防止它发生的一种方法。
三天前,我们搭的正是这一班车。我想起当时我边向窗外看边想:再过几天你就会回来,你将是一个人,你会恨透了那感觉,所以千万别让任何东西乘虚而入。要警醒。我预演过失去他的处境,不只是为了提前一点一点地接受,好抵挡痛苦,也像迷信的人那样,想看看如果我愿意接受最糟的状况,命运会不会减轻摧毁的力度。我像为打夜战而受训的士兵,生活在黑暗中,以免黑暗骤降,无法看清周遭。预演痛苦来抑制痛苦。依循顺势疗法的道理。
暂停片刻。我想说:如果你什么都记得,如果你真的和我一样,那么在你明天离开以前,或即将关上出租车门的瞬间,当你已经向其他每个人都告别,此生已再无其他的话可说时,那么,就这一次,请转身面对我,即使用开玩笑的口吻,或当作事后无意间想起。当我们在一起时,这对我来说可能极为重要。就像你过去所做的那样,看着我的脸,与我四目相视,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差不多一个月之后,当我再度造访罗马,今晚与奥利弗共游此地的事却显得毫不真实,仿佛发生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我身上。
“你们拥有美好的友谊。”这比我预想过的任何说法都大胆许多。
但突如其来的独处的自由,跨越了类似时间障碍的东西,令我呆住了。
如今,我则想知道,我愿意放弃什么,只求时间能倒转回六月末的那个下午,我按照惯例带他参观我家,接着,不知不觉地,我们向废弃铁轨旁炙热的空地走去,在那里我收到了诸多“再说吧”中的第一剂。
“埃利奥。”我重复,意思是我在听,也为了点燃我们过去的游戏,证明自己什么都没忘。“我是奥利弗。”他说。他已经忘了。
不是因为我们想让事情不期然地找上我们,好归咎于机缘,而是想借着不刻意维系感情来避免感情的消逝。
那个吻和你的衬衫,是我从你那里得到的一切。
他打断我:“听着,你有一段美好的友谊。或许超越友谊。我羡慕你。从我的角度来说,大多数父母都会希望这样的事就此烟消云散,或祈求自己的儿子快点重新站起来。但我不是这样的父母。从你的角度来说,如果感到痛苦,就去抚慰,如果有火焰,不要扑灭,也不要残忍地对待。当退缩让我们整夜难眠时,它可能就会是个非常糟糕的选择,但眼见别人在我们愿意被遗忘以前先忘了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为了以远超我们所需的速度被疗愈,我们从自己身上剥夺了太多东西,以致不到三十岁就枯竭了。每次重新开始一段感情,我们能付出的东西就会变得更少。为了不要有感觉而不去感觉,多么浪费啊!”
他突然变得冷淡,仿佛害怕我们是在他不愿想起的地方认识的。他一脸踌躇、讥讽和质疑,还有一抹不自在和不安的微笑,仿佛在预演一场“我恐怕你认错人了”的戏码。
二十年恍如昨日,昨天只比今天早上早了一点,然而早上却似乎有几光年那么远。
我说。“真希望我跟你们大家待在一起。”我回答,为了一个几乎已完全不再想起的人而激动不已。时间让我们变得多愁善感。或许,到头来,令我们受苦的就是时间。
我们点了两杯马提尼(他特别指定了蓝宝石琴酒),紧挨着坐在马蹄形雅座上,像两个因为妻子去化妆室而被迫局促地坐在一起的丈夫。
我不嫉妒先于我而存在的生命,也不渴望回到他正当我这个年纪的时光。
我知道或许我们再也不会拥有这一切,可是我却无法说服自己去相信。
每个人都点了咖啡。我以为我理解大家为何在鹿角咖啡馆附近宣誓,或许我想要自以为自己理解了,可我不确定。我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喜欢那样。或许其他人也不喜欢,却觉得有义务从众,宣称自己不宣誓就活不下去。
惊喜总是伴随着刻意伤人的利刃。
每次回罗马,我都会回到那里。对我来说,过去依旧鲜活,依旧回响着完全属于当下的声音,仿佛从爱伦•坡故事里偷来的心仍在古老的石板路下跳动,并且要提醒我,在这里,我终于和适合自己但却无法拥有的人生邂逅了。
有可能会见到他的家人,让我惊慌失措——太真实,太突然,太直接了,演练得还不够。过去几年来,我一直把他存放在永恒的过去,视他为过去完成式的恋人,将他冰存,以回忆和樟脑丸填满他,就像在与夜的幽灵交谈的动物标本。我偶尔把他拿出来掸一掸灰尘,再放回壁炉架上。他不再属于尘世或生活。此时我发现,不只是我们选择的路相距有多远,还有即将向我袭来的失落有多大,无非是这些东西而已。我不介意用抽象的术语去思考这份失落,但被盯着看却令人心痛。在我们已经不再想起已经失去的,或许可能也不会再在乎之后很久,怀旧之情仍然令人心痛。
我知道我们的时间所剩不多,但我不敢去数;就像我知道这一切将会去往哪里,却不愿意去留意途中的里程碑。这段时间,我刻意不为了回程而撒面包屑;相反地,我把面包屑都吃掉了。说不定他可能是个彻头彻尾的讨厌鬼;当时间和流言最终会挖空我们曾共同拥有的一切,剔除所有,只剩下鱼骨头时,他可能会彻底改变我、毁灭我。我可能会想念这一天,或许我能做得远胜于此,但至少我始终知道,那些下午,在我卧房里,我把握住了属于我的瞬间。
“Cor cordium。这是我此生对别人说过的最真实的话。”
之所以羡慕,是因为‘遗憾’这个词令我们心碎。
我只知道我对他已毫无隐藏。此生我再也没有这样自由和安全过。
去感受你所感受到的东西吧。
“对。”我回答,试着让我的“对”悬在半空中,仿佛被暂时窜出头、但终究会被力压的反方预赛优胜者刺激得情绪高涨一样。我只希望他还没听出我声音里的些微敌意、回避和似乎很疲倦的“对”,所以呢?
“接下来这段时间会很艰难。”他变了变声音,开始说。他的语气告诉我:我们不必讲出来,不过也别假装听不懂我说什么。用抽象的方式表达,是向他道出真相的唯一方式。
他的大学时代——每次他提及——就会拥有万众瞩目、闪闪发亮的魔力,仿佛那些都属于另一段人生,已成过往,而我无缘参与。
他到来。他离去。其他什么都没改变。我没改变,世界没改变。但一切都将不同,剩下的只有梦和奇怪的回忆。
她点了点头,不理会我的讶异,仿佛点头本身就是恶作剧的一部分。
罗马处处可见丘比特,因为我们剪下了他的一只翅膀,所以他不得不在空中盘旋。
当他为他的妻子、为我和为他自己倒酒时,我们俩终究会明白,他比任何时候的我都更像我自己,因为多年前在床上,在他成为我、我成为他之后,在人生的每条岔路上完成使命许久之后,他会是、也将永远是我的兄弟、我的朋友、我的父亲、我的儿子、我的丈夫、我的恋人和我自己。在那年夏天偶遇的几周,我们的人生几乎未受影响,可是我们却跨越到时间静止、天堂降临人间的彼岸,得到从降生以来神注定要赐给我们的那一份。我们望向一边。除了这件事,我们无所不谈。但我们始终知道,现在什么都不说却更确认了这一点。我们已经找到星星、你和我。而这是仅此一次的恩赐。
有些晚上,我把“大波浪”从袋子里拿出来,确认没沾染到塑料或我衣服的味道,然后抱着它,将两只长袖围在身上,在黑暗中低声呼唤他的名字。欧里法、欧里法、欧里法——那是奥利弗模仿马法尔达和安喀斯的古怪腔调,以他的名字呼唤我的声音;那也是我在以他的名字呼唤他,希望他也能以我的名字唤我的声音,我愿意代替他对我唤我的名字,再回应他:埃利奥、埃利奥、埃利奥。
或许是酒精,或许是真相,或许我不想把事情变抽象,总之我觉得我必须说出来,因为现在正是说这句话的时候。因为我明白这是我来这儿的原因,为了告诉他:“在我死去的时候,你是我唯一想要道别的人,因为唯有那时,我所谓的‘我的人生’才有意义。万一我听到你过世的消息,我所知道的自己的人生,还有这个此刻正在跟你说话的我,将不复存在。有时候我脑中会出现这样可怕的画面:我在我们 B城的家醒来,朝海的方向望去,听到海浪传来你已在昨晚过世的消息。我们错过了太多。那就是处于昏迷状态。明天我回到我的昏迷状态,你也回到你的昏迷状态。对不起,我无意冒犯——我相信你的人生里没有昏迷状态。”
他来得正是时候。没有一抹云彩,没有一圈涟漪,没有一丝风。“我都忘了我多爱这个地方了。但这里跟我记得的一模一样。中午的这里是天堂。”
我突然明白,我和他共度的是借来的时光,时间始终是借来的,而就在我们最无力偿还而且需要借得更多的时候,借贷机构却要强索额外费用。
我们随时就会道别。霎时,我生命的一部分就要被带走,再也不会归还。
这是我们的离别预演。仿佛看着一个插着呼吸机的人,而过两天就会被拔掉。
“就一会儿。不过我什么都不想做。”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再说吧,或许吧”的修正更新版。
我可能希望他明白,自从他上次来过之后,一切都没有改变,“天堂的门阶”依然在那儿,通往海边那扇歪斜的门依旧嘎吱作响,世界仍和他离开时一模一样,只是少了维米尼、安喀斯和父亲。这是我想展现出的欢迎。但我也希望他意识到我们现在没必要叙旧。我们在少了彼此陪伴的状况下走过、也经历过太多,彼此已经没有任何共有的底色。或许我希望他感觉到失去的刺痛,以及悲伤。但到头来,或许经由妥协,我断定最简单的办法是表示我什么都没忘。
“那再让我讲一件事。这么做能够扫除我们之间的芥蒂。我或许曾经很接近,却从来没拥有过你所拥有的。总是有什么东西在制止或阻挠我。你怎么过日子是你自己的事。可是切记,我们的心灵和身体是绝无仅有的。许多人活得好像自己有两个人生,一个是模型,另一个是成品,甚至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各种版本。但你只有一个人生,而在你终于领悟以前,你的心已经疲倦了。至于你的身体,总有一天没有人要再看它,更没有人愿意接近。现在的我觉得很遗憾。我不羡慕痛苦本身。但我羡慕你会痛。”
未来的那两人永远无法抹除、撤销、忘却或重温过去——过去就困在过去,像夏日黄昏将近时原野上的萤火虫,不断在说:你原本可以如此。但回头是错。向前是错。看开是错。努力纠正所有的错,结果同样是错。
我倾向于一种信念,那就是,生活有时足够仁慈,能够给予我们有效的隐喻来帮助我们看清自己是谁,渴望什么,又要去往何方。可是隐喻是一回事,生活又是另一回事。
可是相反,我把细微事物收集起来,好在未来贫瘠的日子里,让过去的微光带给我温暖。我开始不情愿地从当下窃取事物,好偿付未来将背负的债务。
他们的人生就像错乱的回音,永远埋藏在封闭的密特拉神殿里。
“这本来是我的,但你拥有它的时间远远超过我。”我们曾经属于彼此,但因为距离如此遥远,所以我们如今已经属于其他人了。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说,唯有擅自占用者才是真正的债权人。
“我拒绝过好多人。从来没追求过任何人。”“你追过我。”“是你让我追的。”
“我想跟全泰国的人睡个遍。结果,全泰国都在跟我调情。你每走一步都难免踉跄倒向某个人。”
感觉我们就像两条裸露却通电的电线,只要彼此轻触就会冒出火花。
在痛苦前,思考痛苦的意义。
当时他在亚洲旅行,所以信寄到的时候,他对维米尼过世的反应与其说是安抚了尚未愈合的伤口,不如说更像是轻轻擦破了已经愈合的伤口。
“就像每个为我们留下终生难忘印记的经验,我感到自己被掏空,被肢解了。这是我过去生命经历的总和。还有,周日下午边唱歌边为家人朋友炒青菜,是我没错;在冰冷的夜晚醒来,只想匆忙披上长袖运动衫赶到书桌前,写下不为人知的自己,是我没错;渴望与另一个人一起赤身裸体,或渴望遗世独立,是我没错;当我的每个部分似乎都天差地远,但它们又都发誓自己能承载我的名字,是我没错。
我看着其他申请者的脸。这个也不差。我开始好奇,若换作其他人来,我的人生会有什么转变。我大概就不会去罗马了。但我可能会去其他地方。我可能会对圣克莱门特一无所知。我可能会发现其他我已错过而且再也无从知晓的东西。也可能不会有改变,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今天的我,可能会成为另一个人。
我努力装出老成世故又极其了解自己的样子,摆出对现实不再抱幻想的讥讽态度。
我能够将自尊轻易丢在他脚边,只要他愿意弯腰捡起,我将心满意足而别无所求。
昨晚的这句话曾经那么真切,现在却只是我拼命为其赋予意义的两个字。
我希望他离开我们家,好让这一切有个了断。
或许我们首先是朋友,然后才是恋人。但话说回来,或许恋人就是如此。
我看着他。感觉像个孩子用尽一切委婉恳求和暗示的办法,却无法让父母想起曾经答应带他去玩具店一样。不需要拐弯抹角。“我只是希望我们能一起去。”
收拾的动作很快,没有一丝后悔或内疚,有如卸掉一个坏掉的灯泡,挖出曾是宠物如今却被宰杀的羊的内脏,或是抽掉逝者床铺上的床单和毯子。拿去,接好,把这些东西丢到看不见的地方。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的银制餐具、他的餐垫、他的餐巾,他的存在,全部消失。此情此景不折不扣地预示了不到一个月后将要发生的事。
我记起我曾在阳台上差点抱住他,但想到我们这样冷战了一天之后,拥抱显得不合时宜才及时罢手。因为当你们一周几乎没握过手时,对方说“我们午夜见”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不假思索地拥抱他。我想起自己敲门前的内心挣扎:拥抱,不抱,拥抱。
大家被他的幽默逗笑,不是因为他有趣,而是因为他无意间流露出了企图有趣的渴望。他只不过是用幽默来拉拢自己无法说服的对象而已。
那天我甚至要自己卸下防备,像其他人一样表现自己的悲痛。但我也不让任何人猜到我心里有远远更为隐秘和沉痛的哀伤,直到我几乎感到可耻地意识到,那部分的我其实并不那么在乎他的死活,一想到他浮肿的、紧闭双眼的遗体终于被冲回岸边,我甚至有近乎兴奋的感觉。
我设法让心静下来,想想我们眼前的落日,像个即将接受测谎的人,借由想象宁静与平和的场景来掩饰自己的焦虑。
耗上半天眼睁睁看着我的整个人生悬而不决。我多么痛恨等待,痛恨为别人一时的兴致所左右。
那年我十七岁,桌上年纪最小,讲话可能最没人听,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尽可能将最多的信息暗藏于最少的字句中。
或许我为了引她说真话,故意忽视她的每一个暗示——害羞与无能的人称之为策略。
我描述着两年前看过的基娅拉的裸体。我想挑逗他。他欲望的对象是谁不重要,只要他被挑逗就好。我也跟基娅拉描述他,想看她的欲望被挑起时,是否跟我一样,好让我根据她的反应来描摹我自己的,看看谁才是真爱。
我非常想要,可是我一旦开始或许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所以我宁可不要开始。
我问他想去看吗?“再说吧。或许吧。”真是有礼的冷淡,仿佛他察觉出我在以过分的热情去讨好他,便立刻把我推开。
他看穿了每一个人,但他之所以能看穿,正是因为他在别人身上最先看到的,恰恰是他在自己身上已经看到却不愿被人发现的东西。
但一切的开始也可能比我想的要晚了许多,在我浑然不觉的时候。你看见一个人,但你其实没真看到他,他还在幕后,正准备登场;或者你注意到他了,可是没有心动,也没有“火花”,甚至在你意识到某个存在或有什么在困扰你之前,你所拥有的六个星期就快成为过去,而他若非已经不在,就是即将离开。实际上,你在慌乱地接近自己也不知情的东西,它已经在你眼皮子底下酝酿了数周,而且所有的征兆都让你不得不呼喊我想要。你会问自己:怎么没能早点明白?我一向清楚欲望为何物啊。然而,这次它悄悄溜过,不着痕迹。我喜欢他每次看破我心思时,脸上闪现的那一抹狡黠的笑,而我真心渴望的其实只是肌肤,只是肌肤。
我想保存的是他声音里汹涌的喘息,那声音后来又萦绕我多日,并告诉我,如果我这一生每夜都能让他这样出现在梦里,我愿意将我的一生赌在梦上,把现实的一切都放弃。
他脸上的表情好似士兵带上战场的爱人的抓拍照,不仅为了让他们记得人生中的美好,以及幸福正在等待着他们,也为了提醒他们,如果躺在运尸袋里返乡,生活绝对不会原谅他们。
我应该学着回避他,切断每个联系,一个接一个,像神经外科医生将一个神经元和另一个分开那样,不再许下那些自我折磨的心愿。
或者,我可能对于这一切要往何处发展,看得不够明白,宁可让事情不知不觉过去。再度沉默。直到他下次开口。
这念头就像舒爽的乳液,首先对你的四肢起作用,然后渗透到你身体的其他部分。它会提供给你各种论点,或支持,或反对,起初都是些幼稚说法,例如“今晚做什么都已太晚啦”之类的,然后上升至一些稍严肃的想法,比如“你如何面对他人,你就如何面对自己”。
但热情容许我们将更多东西隐藏起来,那一刻在莫奈的崖径上,我想把关于我的一切隐藏在这个吻里,我也渴望自己迷失在这个吻里,就像一个人希望脚下的大地裂开,然后将自己完全吞没。
“喜欢看书的人善于隐藏自我。隐藏自我的人未必喜欢自己。”
然而,下一次偶然碰到他,我只想对他表达感谢。我在表达感谢的同时,能否不令人觉得困扰或有负担?还是说,只要是“感谢”,无论多么克制,总带有丝丝多余的甜腻,让地中海式热情难免显得多愁善感又矫揉造作?不能适可而止,不能低调,一定要大肆声张,昭告天下,慷慨陈词。
在我有机会故意拉大我们之间的距离前,我感觉自己就像被花店临街橱窗上流动的水冲洗过一样,所有的害羞与压抑都被带走了。无论紧张与否,我已经懒得盘问自己的每一个冲动。如果我蠢,就让我蠢到底吧。如果我碰到了他的膝盖,那就碰着吧。如果我想拥抱,那就拥抱吧。
但现在我仿佛置身天堂。因为他没忘记我们有关策兰的对话,这让我前所未有地狂喜了好几天。
年轻如我,也知道这不会持久,我至少应该享受当下,而不是一再地用古怪的方式去试图巩固我们的友谊,或将之提升到另一个层次,结果搞砸一切。没有什么所谓的友谊,那没意义,只是一时的恩宠。
不把我不顾一切渴望给予的东西给他,或许是我这辈子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
我忘记在那个许诺里加的注是:冰霜和冷淡有的是办法,能立即撤销所有在晴朗日子签署的休战书。
我耸耸肩,表示不把敷衍的感谢当一回事。或许我只是希望他再说一次。
下山途中,经过“我的天地”,这次换我故意望向一边,仿佛我早已把那件事抛诸脑后。我相信如果当时我看他,我们会交换同样有感染力的微笑,那种提起雪莱之死时立刻从脸上抹掉的微笑。我们的距离可能因此拉近,只要提醒我们此刻需要保持多远的距离。或许故意望向一边并且清楚我们是为了避免“说话”才望向一边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找到相视而笑的理由,因为我确信他知道,我了解他明白我在避免提到莫奈的崖径,也确信这种无不透露着分离的回避,反而成了我们完美同步的亲密时刻,谁都不希望会消散。
我几次试着学他那样出门,可是我太沉浸于自我的感觉里了,像一个光着身子在更衣室走动的人原是想让自己更加自然,到头来却被自己的裸体勾起了性欲。
当晚在日记里,我写道:我说我认为你讨厌那部作品,是夸张了点。我真正想说的是:我认为你讨厌我。我希望你说服我,事实正好相反,你也的确这么做了一下。但为什么我明天早上就会不再相信?
把吸管像扔飞镖一样插进去。
或许看他和别人这样跳舞,让我明白他已有所属,就没有理由再抱希望。这是好事,可以帮助我复原。或许这么想已经是复原的前兆。我曾试图偷食禁果,现在却得到从轻发落。
“不会啊。”我回答。但对于一个诚心发问的人来说,我回答得太快了。为了减轻“不会啊”的含糊性,我又说我今天可能要睡一整天。“我觉得我今天没法去骑车了。”
此举刺痛了我。
如果心神不宁带来的失落感越积越多,那么一个人是否能够带着宽恕与慈悲,学着寻找将其视为常态的方式?
“你说话的时候看着他,他却总是撇开目光,没专心聆听,他只想趁忘记以前,赶紧说出你发言时他在心里演练过的话。”
拒绝大家普遍认可的,只会让他们察觉到,我实则隐瞒了需要抗拒他的真实想法。
就像是从一团可怕的梦魇中缓慢降落,但还没有完全着陆,也不确定是否想要着陆,因为尽管我知道自己无法继续与那团巨大又奇形怪状的梦魇相抗衡,而且那团梦魇仿佛是曾飘进我生命里的自我厌弃和自责之云中最大的一朵,但是降落之后等待着我的一切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新欢的痛苦、郁热和震颤,眼看就能获得的美满幸福,却仍在咫尺之外徘徊;在他身边总是坐立不安,怕领会错他意思,担心失去他,遇事都要揣测再三;想要他也想被他要,使出各种诡计;架起重重纱窗,仿佛自己与世界之间立着不止一层的纸拉门;急吼吼地把本来就不算事的事儿煞有介事鼓捣一番后又装作若无其事——这些症状,在奥利弗来到我家的那个夏天,全都发生了。
但我也知道,如果他今晚出现,那么即将发生的事,无论是什么,即使一开始不合我的意,我也会让自己去经历,直到最后。
我敲了敲玻璃窗,轻轻地。我的心狂跳。我什么都不怕,那为何如此慌乱?为何?因为一切都令我害怕,因为恐惧和欲望都忙着对彼此、对我躲躲闪闪,我甚至无法辨别“想要他开门”和“希望他爽约”之间有什么不同。
每个人都会经历一段误入 traviamento的时期,比方说,当我们转变人生方向或选择另一条路的时候。但丁就是这样。有些人知错能改,有些人假装反省,有些人一去不复返,有些人甚至还没开始就退缩,还有一些人因为害怕任何改变,最后才发现自己度过了错误的一生。
我刻意不去计算时间。起初是因为我不愿意去想他会和我们相处多久,后来则是因为我不想面对他在这里的日子越来越少。
就连没那么精明的人类灵魂观察者,也能在我的执意否认中,看出我只是拿基娅拉当幌子。
“你来这里做什么?”他一看到我就说。他用玩笑来隐藏自己并试图掩饰我们已经完全不交谈的事实。低劣的伎俩,我想。
大家吵吵闹闹,结果我们漏看的剧情比奥利弗因为那通简短电话错过的还要多。
我从来没想过,如果他随口一句话就能让我如此幸福,那么,他再说一句,我就会神魂颠倒。如果我不想痛苦,那么,我就应该学会留心这小小的喜悦。
既然两人手中的牌全摊在桌上了,现在感觉就像闲聊一样。
不确定他是否一同晚餐,是一种折磨,却是可忍受的。不敢问他来不来,才是真正的酷刑。
过去从没人道别时跟我说“再说吧”的。听来刺耳、草率、轻蔑,里边挟有一层漠然,感觉能否再见到你,能否再收到你的音信,都无所谓。
大家都在这里做什么?不做什么。就是等夏天结束。
从第一次弹,我就很清楚这部作品的哪个乐句撩拨了他。每当我演奏到那一段,都把它当作一份小礼物送给他,因为那的确是献给他的,那象征着我生命中美妙的地方,不需要天赋就能理解,而且激励我往乐曲里加入一段长长的华彩乐章。只为了他。
我喜欢他在书店里的一举一动。他带着好奇却不完全专注,兴趣满满却保持冷静,在“看我找到了什么”和“当然,怎么可能有书店不卖这种书”之间剧烈摇摆。
比起他的热情奔放、随性所至,我的欲望有多么曲折又遮遮掩掩。
然而令我心烦意乱的,并不是挽回自己形象所要耗费的周章,而是我终于,带着几许让人不快的担忧,迟迟省悟:无论当时,还是我们在铁轨旁闲聊时,我毫不掩饰,但也不愿承认的是,我一直在试图赢得他的心——却徒劳无功。
我羡慕他有自我贬抑的特权。
用语刻意折中,因为我知道,谈到他时使用点障眼法,就没人会起疑心。
“你没事吧?”“我想我没事,很快就会好。”我在太多小说里看过太多角色讲这种话。这种话让负心人得以免责,给每个人保留颜面,让无处躲藏的人重获尊严与勇气。
我不是没猜过她的心思,可是我不敢相信她把我看得这么透彻。或许是害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才使我不想相信她所暗示的事。我是故意不老实吗?我能在问心无愧的状况下,继续曲解她的话吗?
我怕他出现又怕他不出现,怕他看我又更怕他不看我。
我没意识到的是,试探欲望的诡计,只不过是想,在不承认自己的欲望的情况下,得到自己想要的。
但打定主意要采取行动而非坐以待毙,让我觉得自己已经做了什么,好像我还没投资,更别说赚钱,却已经开始觉得自己在盈利了。
“发生什么事了?”我以提问的方式笨拙地说。“没事。”我又多想了一下。“没事。”我再一次重复——仿佛我开始隐约领会到的事是如此杂乱无章,只要借着重复“没事”这句话,就能被轻易推至一旁——从而填满令人难堪的沉默裂隙。“没事。”
我很愿意给他烙上难缠、拒人千里的印记,然后与他再无瓜葛。但他的只字片语,又让我眼见自己,从摆臭脸变成我什么都愿意为他弹,直到他喊停,直到午餐时间,直到我手指上的皮一层一层剥落,因为我喜欢为他效劳,愿意为他做任何事,只要他开口。我从第一天就喜欢上他,即使他以冰冷回应我重新献上的友谊,我也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之间的这次对话,以及不乏让暴风雪远去、重新找回夏天的简单方法。
我听得笑了起来,转眼间,我全身赤裸,感觉到床单轻轻落在我的下体上,而这世界已再无秘密,因为渴望和他上床是我唯一的秘密,而此刻我正同他分享着这个秘密。感觉到他的手伸进被单在我的全身游移,是多么美妙啊,我们的一部分就像已在求爱派对上达至亲密,而暴露在被单外的那部分,仍然在跟得体的礼节抗争着,好比在拥挤的夜总会里,其他人已经在暖手了,而迟到者依然冷得直跺脚。
我始终尽力把他留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我不会让他溜走,除非他不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不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倒是不太在意他在做什么,只要他跟别人在一起时,别变了个样子就好。他离开时,不要变成其他模样,不要变成我从未见过的人。除了他跟我们、跟我在一起时,我所知道的那个人生之外,别让他有其他的人生。
我喜欢我们的心像是在并肩而行的样子,我们总能立刻猜出对方在玩什么文字游戏,却到最后一刻才说破。
我突然想到,我之所以决定不要太快疏远他,不只是为了避免伤害他的感情,或避免让他忧虑,也不是为了避免引发家中尴尬棘手的局面,而是因为不确定几小时之内,我会不会再度不顾一切地想要他。
那天早上,我在我的日记里写下这句话,却略过不写那是我梦见的。我希望多年以后重读日记,相信他真的曾对我这般恳求,哪怕片刻也好。
我多么喜欢他那样重复我刚刚说过的话。那让我觉得像是一个爱抚,或一种手势。第一次完全是偶然,第二次便是刻意为之,第三次更是如此。
让我知道愿望落空的感受,就像从活泼的蝴蝶身上剪掉翅膀一般。
如果我现在看,我这天就毁了。但如果我晚一点再看,这一整天也变得没有意义,无法思考其他任何事情。
他的坦诚似乎打开了我们之间所有的排水管道,却也恰恰淹没了我刚萌芽的希望。此后我们将何去何从?还有什么好说的?
就像是要公开宣称一个人拥有无法抗拒的魅力,以便隐藏自己想要拥抱他的渴望那样。
他的生活就像他的论文一样,尽管怎么看都让人觉得混乱,实则总是一丝不苟地界限分明。
我脑海中存在已久的构想如今要在真实世界上演,不再漂浮于永恒的模棱两可之地。我感觉像是一个进了刺青店的人,最后一次凝视自己光洁的左肩。
但我也知道,我是在用回头再试为人生筑起一道防线,几个月,几个春夏秋冬,一年又一年,整整一生就这样过去,除了铭刻在每一天的“回头再试”之外,什么都没有发生。
希望这个夏天永不结束,希望他永不离去,让音乐永远无限循环下去。
二十年恍然隔日,昨日只比今天早上早了一点,然而早上却似乎有几光年那么远。
我把细微的事物收集起来,好在未来贫瘠的日子里,让过去的微光带给我温暖。我开始不情愿地从当下窃取事物,好偿付未来将背负的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