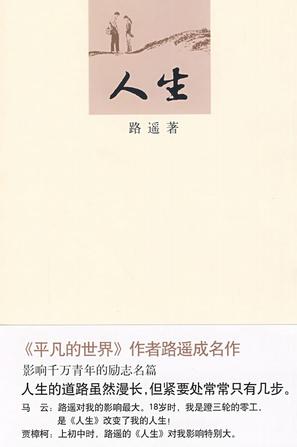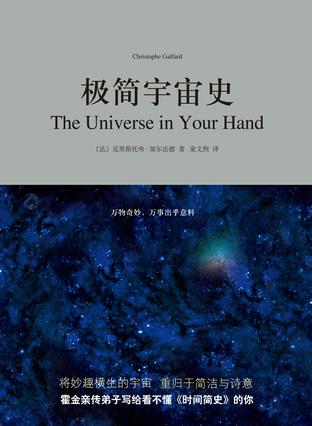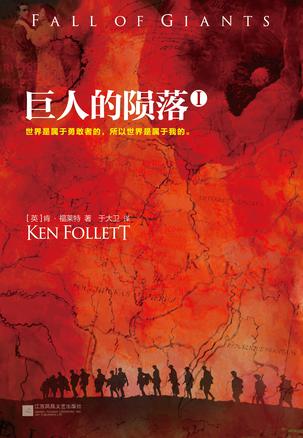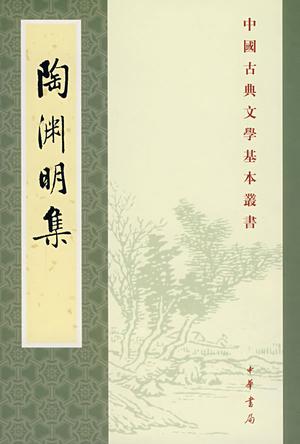简爱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
-
好书网为大家整理了经典好书《简爱》中的经典语录,精彩段落及优美句子,重读经典,感悟人生。让读者沉浸在自己的阅读世界里,忘记周围的世界, 与作者一起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快乐、悲伤、愤怒、平和,欢迎大家阅读~

我进门的时候,图书室显得很安静,那女巫--如果她确实是的话,舒适地坐在烟囱角落的安乐椅上。她身披红色斗篷,头戴一顶黑色女帽,或者不如说宽边吉卜赛帽,用一块条子手帕系到了下巴上。桌子上立着一根熄灭了的蜡烛。她俯身向着火炉,借着火光,似乎在读一本祈祷书般的黑色小书,一面读,一面象大多数老妇人那样,口中念念有词。我进门时她并没有立即放下书来,似乎想把一段读完。
过了好一会儿,帐幕才再次拉开。第二幕表演比第一幕显得更加精心准备。如我以前所观察的那样,客厅已垫得比餐室高出两个台阶,在客厅内靠后一两码的顶端台阶上,放置着一个硕大的大理石盆,我认出来那是温室里的一个装饰品--平时里面养着金鱼,周围布满了异国花草--它体积大,份量重,搬到这儿来一定是花了一番周折的。
罗切斯特先生拉开厚厚的窗幅,掀起亚麻布窗帘,尽量让月光射进屋来。看到黎明即将来临,我既惊讶又愉快。多漂亮的玫瑰色光束正开始照亮东方的天际!随后,罗切斯特先生走近梅森,这时外科医生已经在给他治疗了。
他的举止很客气,但说话的腔调听来有些异样——不是十足的外国腔,但也不完全是英国调。他的年龄与罗切斯特先生相仿——在三十与四十之间。他的肤色特别灰黄,要不然他倒是个英俊的男人,乍看之下尤其如此。仔细一打量,你会发现他脸上有种不讨人喜欢,或是无法让人喜欢的东西。他的五官很标准,但太松弛。他的眼睛大而悦目,但是从中透出的生气,却空洞乏味——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在这种情形下,我既得细听又得静观,细听有没有野兽或者那边窠穴中魔鬼的动静。可是自从罗切斯特先生来过之后,它似乎已被镇住了。整整一夜我只听见过三声响动,三次之间的间隔很长--一次吱吱的脚步声,一次重又响起短暂的狗叫似的声音,一次人的.深沉的呻吟声。
我回到房间,从脸盆架上找到了海绵,从抽屉里找到了食盐,并顺原路返回。他依旧等待着,手里拿了把钥匙。他走近其中一扇黑色的小门,把钥匙插进锁孔,却又停下来同我说起话来。
这老太婆在帽子和带子底下爆发出了一阵笑声。随后取出一个短短的烟筒,点上烟,开始抽了起来。她在这份镇静剂里沉迷了一会儿后,便直起了弯着的腰,从嘴里取下烟筒,一面呆呆地盯着炉火,一面不慌不忙地说:“你很冷;你有病;你很傻。”
我不喜欢同一念头反复不去——不喜欢同一形象奇怪地一再出现。临要上床和幻象就要出现的时刻,我便局促不安起来。由于同这位梦中的婴孩形影不离,那个月夜,我听到了一声啼哭后便惊醒过来。第二天下午我被叫下楼去,捎来口信说有人要见我,等候在费尔法克斯太太房间里。我赶到那里,只见一个绅士仆人模样的人在等我,他身穿丧服,手中拿着的帽子围着一圈黑纱。
这老太婆在帽子和带子底下爆发出了一阵笑声。随后取出一个短短的烟筒,点上烟,开始抽了起来。她在这份镇静剂里沉迷了一会儿后,便直起了弯着的腰,从嘴里取下烟筒,一面呆呆地盯着炉火,一面不慌不忙地说:“你很冷;你有病;你很傻。”
他的举止很客气,但说话的腔调听来有些异样--不是十足的外国腔,但也不完全是英国调。他的年龄与罗切斯特先生相仿--在三十与四十之间。他的肤色特别灰黄,要不然他倒是个英俊的男人,乍看之下尤其如此。仔细一打量,你会发现他脸上有种不讨人喜欢,或是无法让人喜欢的东西。他的五官很标准,但太松弛。他的眼睛大而悦目,但是从中透出的生气,却空洞乏味--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在拆开封口仔细看信时,我继续喝我的咖啡(我们在吃早饭)。咖啡很热,我把脸上突然泛起的红晕看作是它的缘故。不过,我的手为什么抖个不停,为什么我情不自禁地把半杯咖啡溢到了碟子上,我就不想去考虑了。
他和搭档们退到了帐幔后头,而由登特上校领头的一组人,在排成半圆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其中一位叫埃希顿先生的男士,注意到了我,好像提议我应当加入他们,但英格拉姆夫人立即否决了他的建议。
莉娅摇了摇头,于是谈话嘎然而止。我从这里所能猜测到的就是这么回事:在桑菲尔德有一个秘密,而我被故意排除在这个秘密之外了。
我的脉搏停止了,我的心脏不再跳动,我伸出的胳膊僵住了。叫声消失,没有再起。说实在,无论谁发出这样的喊声,那可怕的尖叫无法立即重复一遍,就是安第斯山上长着巨翅的秃鹰,也难以在白云缭绕的高处,这样连叫两声。那发出叫声的东西得缓过气来才有力气再次喊叫。
我回到房间,从脸盆架上找到了海绵,从抽屉里找到了食盐,并顺原路返回。他依旧等待着,手里拿了把钥匙。他走近其中一扇黑色的小门,把钥匙插 进锁孔,却又停下来同我说起话来。
平常我是拉好帐幔睡觉的,而那回却忘了,也忘了把百叶窗放下来。结果,一轮皎洁的满月(因为那天夜色很好),沿着自己的轨道,来到我窗户对面的天空,透过一无遮拦的窗玻璃窥视着我,用她那清丽的目光把我唤醒。夜深人静,我张开眼睛,看到了月亮澄净的银白色圆脸。它美丽却过于肃穆。我半欠着身子,伸手去拉帐幔。
最奇怪的是,除了我,房子里没有人注意到她的习惯,或者似乎为此感到诧异。没有人谈论过她的地位或工作,没有人可怜她的孤独冷清。
我给了她一个先令。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旧长袜,把钱币放进去,用袜子系好,放回原处。她让我伸出手去,我照办了。她把脸贴近我手掌,细细看了起来,但没有触碰它。
我按他的吩咐办了。宾客们都瞪着眼睛看我从他们中间直穿而过。我找到了梅森先生,传递了信息,走在他前面离开了房间。领他进了图书室后,我便上楼去了。
猜谜的一方再次交头接耳起来,显然他们对这场戏所表现的字或只言片语,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他们的发言人登特上校要来表现“完整的场面”,于是帷幕又一次落下。
我的脉搏停止了,我的'心脏不再跳动,我伸出的胳膊僵住了。叫声消失,没有再起。说实在,无论谁发出这样的喊声,那可怕的尖叫无法立即重复一遍,就是安第斯山上长着巨翅的秃鹰,也难以在白云缭绕的高处,这样连叫两声。那发出叫声的东西得缓过气来才有力气再次喊叫。
夜晚的宁静和安逸,被响彻桑菲尔德府的一声狂野刺耳的尖叫打破了。
我不喜欢同一念头反复不去--不喜欢同一形象奇怪地一再出现。临要上床和幻象就要出现的时刻,我便局促不安起来。由于同这位梦中的婴孩形影不离,那个月夜,我听到了一声啼哭后便惊醒过来。第二天下午我被叫下楼去,捎来口信说有人要见我,等候在费尔法克斯太太房间里。我赶到那里,只见一个绅士仆人模样的人在等我,他身穿丧服,手中拿着的帽子围着一圈黑纱。
五月一日下午五点左右,我到了盖茨黑德府门房,上府宅之前我先进去瞧瞧。里面十分整洁,装饰窗上挂着小小的白色窗帘,地板一尘不染,炉栅和炉具都擦得锃亮,炉子里燃着明净的火苗。贝茜坐在火炉边上,喂着最小的一个孩子,罗伯特和妹妹在墙角不声不响地玩着。
暴力不是消除仇恨的最好办法,同样,报复也绝对医治不了伤害。
即使整个世界恨你,并且相信你很坏,只要你自己问心无愧,知道你是清白的,你就不会没有朋友。
第一次报复人,我尝到了滋味,像喝酒似的。刚一喝,芬芳甘醇,过后却满嘴苦涩。
对心灵如水,既柔顺又稳重,既驯服又坚强,可弯而不可折的人,我会永远温柔和真诚。
怜悯,不过是内心自私无情的人,听到灾祸之后所产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痛苦,混杂着对受害者的盲目鄙视!
我越是孤独,越是没有朋友,越是没有支持,我就得越尊重我自己。
要自爱,不要把你全身心的爱,灵魂和力量,作为礼物慷慨给予,浪费在不需要和受轻视的地方。
真正的世界无限广阔,一个充满希望与忧烦,刺激与兴奋的天地等待着那些有胆识的人,去冒各种风险,追求人生的真谛。
那些无论我做什么去讨他们的欢心都始终厌恶我的人,我也应该厌恶他们;对那些不公平的惩罚我的人,我就应该反抗。
假如你避免不了,就得去忍受。不能忍受生命中注定要忍受的事情,就是软弱和愚蠢的表现。
我贫穷,卑微,不美丽,但当我们的灵魂穿过坟墓来到上帝面前时,我们都是平等的。
在你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你常常会发现不由自主地被当作知己,去倾听你熟人的隐秘。你的高明之处不在于谈论你自己,而在于倾听别人谈论自己。
我无法控制自己的眼睛,忍不住要去看他,就像口干舌燥的人明知水里有毒却还要喝一样。我本来无意去爱他,我也曾努力的掐掉爱的萌芽,但当我又见到他时,心底的爱又复活了。
你以为我贫穷、相貌平平就没有感情吗?我向你发誓,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会让你无法离开我,就像我现在无法离开你一样。虽然上帝没有这么做,可我们在精神上依然是平等的。
我曾那么爱罗切斯特先生,还几乎把他当成了上帝。虽然现在我也不认为他是邪恶的。但我还能再信任他吗?还能回到他身边吗?我知道我必须离开他。对我来说他已不是过去的他,也不是我想象中的`他了。我的爱情已失去,我的希望已破灭。我昏昏沉沉的躺在床上,只想死去。黑暗慢慢把我包围起来。
如果上帝赐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会使你难以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以离开你。上帝没有这么做,而我们的灵魂是平等的,就仿佛我们两人穿过坟墓,站在上帝脚下,彼此平等—本来就如此!
如果上帝赐予我财富与美貌,我会使你难以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以离开你。上帝没有这么做,而我们的灵魂是平等的,就仿佛我们两人穿过坟墓,站在上帝脚下,彼此平等—本来就如此!
我曾那么爱罗切斯特先生,还几乎把他当成了上帝。虽然现在我也不认为他是邪恶的。但我还能再信任他吗?还能回到他身边吗?我知道我必须离开他。对我来说他已不是过去的他,也不是我想象中的他了。我的爱情已失去,我的希望已破灭。我昏昏沉沉的躺在床上,只想死去。黑暗慢慢把我包围起来。
谁说现在是冬天呢?当你在我身旁时,我感到百花齐放,鸟唱蝉鸣。
你以为我会无足轻重的留在这里吗?你以为我是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人吗?你以为我贫穷、低微、不美、缈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和你有一样多的灵魂,一样充实的心。如果上帝赐予我一点美,许多钱,我就要你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我现在不是以社会生活和习俗的准则和你说话,而是我的心灵同你的心灵讲话。
更多文摘
- 1. 我们内心的冲突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
- 2. 雪莱抒情诗选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
- 3. 独步天下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
- 4. 艺术通史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
- 5. 魔力的胎動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
- 6. 远航船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
- 7. 最后的天空之后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
- 8. 战争论(全三卷)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
- 9. 臺北人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
- 10. 钱文忠说佛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
- 11. 夜行记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