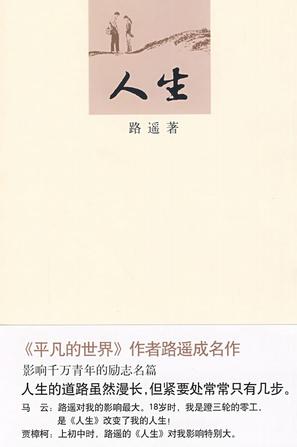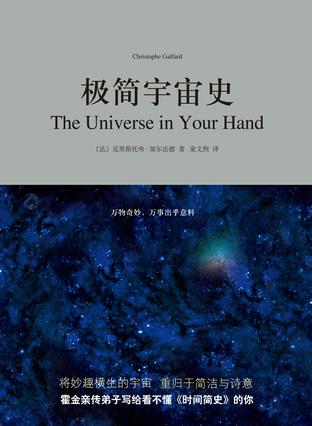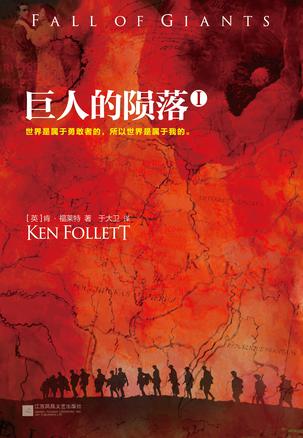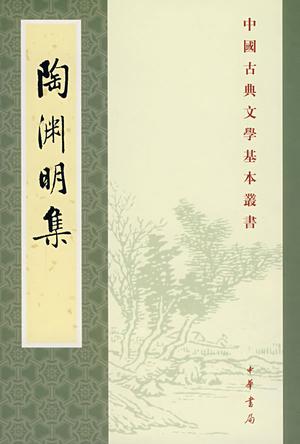-
他起身要走,才走几步,子柚挣扎几番,叫了他一声:“周黎轩!”她一字字喊得清晰无比。
-
在我年轻常犯错误的时候,我常常希望幸福了就死,因为在最初的成功之中有一种至福,使我渴望着毁灭。 … 我还预感到我未来命运的种种苦难,由于精于为自己铸造痛苦,我就置身于两种绝望之间:有时候我认为我不过是个废物,不能超出于平庸之上;有时候我似乎觉得我身上有些品质永远得不到欣赏。一种隐秘的直觉告诉我,我在这个世界上往前走,根本找不到我寻找的东西。
-
时间在改造一切,星宿的运行,昆虫的触角、你和人,同样都在时间下失去了固有的位置和形体。尤其是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
-
布雷弗耐的街道上空无人迹。酷热造成一种令人恶心的午睡气氛,直从天上压下来。一道阴影勉强遮着半边人行道,可眼下已被酷热蚕食将尽,烤得半熟。
-
……他边走边竭力寻找《特里斯坦》最后一幕序曲动机的名称。
-
上午九时半,抵达上海。刚踏上朋友今鹰家的楼梯,突然有人在下面大声叫喊,转身一看,是山本实彦。太意外了,本想下去说说话,但一想还没跟今鹰打招呼,就上了二楼,喝了杯茶后,去楼下的内山书店。书店里有鲁迅、实彦以及内山书店老板三人。鲁迅因为昨晚赶写《改造》的稿子,一直没睡,脸色苍白,胡须浓密,牙齿长得很整齐。他邀我一起上南京路新雅饭店吃午餐。
-
“让我们的知识 定出这样一个合理的价格,以致世人可相信 诗人的警句,不再断言 每种艺术只是它自己的奉承者。”
-
独立且带有本体论意义的“制度”既然是近代一种参照西方产生的概念,将不同时代的“制度”衔接起来形成的“制度史”成为这种制度观的历史投影,其能否独立存在就要打个问号。我们需要将这种后见之明“悬置”起来,返归古代王朝的具体时空,回到人(无论是圣人、君王还是官员、百姓)/事关系,甚至天道/人事关系中,去认识制度的产生、实态及其变化。
-
搁置概念化的抽象认识与结构性的解释框架,将动态的、由具体人的活动汇聚而成的统治作为观察对象,分析反复发生的事务,看它们如何将人的言行衔接起来,形成惯例,构成约束人的结构,不失为一种适切的选择。P210
-
人类有生存本能,更有自我毁灭的欲望,达到完美平衡时,就是美好的生活。
-
几个女大学生连说带笑地拥了进来,店里的空气也顿时变得活跃了。正是令人羡慕的年纪啊。不过你们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等你们一离开学校,也会变成我这样,一边打工拿着最低时薪,一边找工作。想到这里,她不由得感慨自己老了,心情愈发沮丧。二十七岁的晚秋,要特长没特长,要钱没钱,要男朋友没男朋友…再过几年,就三十岁了。而三十这个数字也意味着青春已经走到了尽头。
-
曾经,我们的童年绵长无尽。 所有已经缩水的、褪色与洗尽的事物都能够测量童年。 那些无法在使用的衣物被清洗、烫平、折叠整齐放在纸箱里,仿佛一种圣物。 然而,假如不从远距离观察,假如没有在一定的时间之外观察(比如说半年),成长本身其实是不可测的。我们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会突然蹿高了。 近看,仿佛一切从未改变过。
-
倘若你高抬贵手,容我听其自然,我就会半睡半醒地了此一生。
-
读书之法,以经为主。苟经术深邃然后观史。观史则能知人之贤愚,遇事得失亦易明了。故凡事可论贵贱老少,惟读书不问贵贱老少。读书一卷,则有一卷之益;读书一日,则有一日之益。
-
……多读书则嗜欲淡,嗜欲淡则费用省,费用省则营求少,营求少则立品高。
num376-390
共89701
相关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