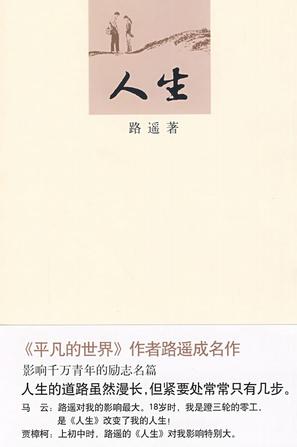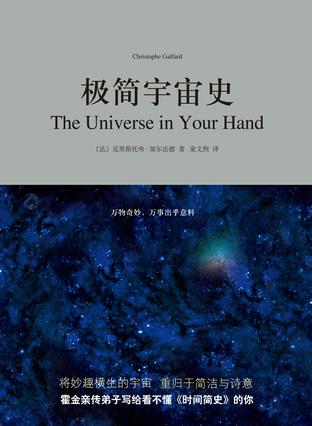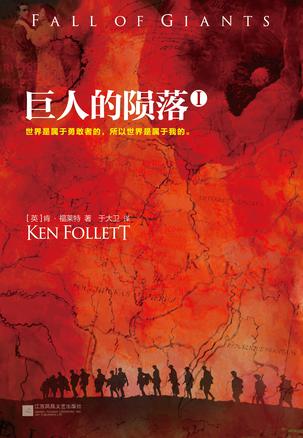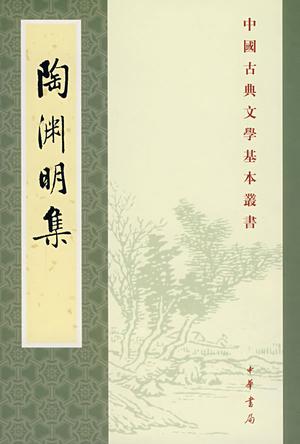色,戒经典语录及段落句子摘抄
-
好书网为大家整理了经典好书《色,戒》中的经典语录,精彩段落及优美句子,重读经典,感悟人生。让读者沉浸在自己的阅读世界里,忘记周围的世界, 与作者一起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快乐、悲伤、愤怒、平和,欢迎大家阅读~

上了船,隔了海洋,有時候空間與時間一樣使人淡忘。怪不得外國小說上醫生動不動就開一張一旅行一的方子,海行更是外國人參,一劑昂貴的萬靈藥。
裏的燈光永遠像是微醺。牆壁如同一種粗糙的羊毛呢。那穿堂裹,望過去有很長的一帶都是暗昏昏的沉默,有一種魅艷的荒涼。
世舫微微鞠了一躬,转身就走了。长安觉得她是隔了相当的距离看这太阳里的庭院,从高楼上望下来,明晰、亲切,然而没有能力干涉,天井、树、曳着萧条的影子的两个人,没有话一一不多的一点回忆,将来是要装在水晶瓶里双手捧着看的——她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爱。
然而盡管兩個人都是很痛苦,蠟燭的嫣紅的火苗卻因為歡喜的緣故顫抖著。
論長相,也就是個踩扁了的李察遜太太,臉橫寬,身材也扁闊,不過有南國佳人的乳房,而且廣東人硬棚一,面部線條較強有力,眉目挺秀些,眼睛裏常有一種憤懣不平之氣。
你的特点是低头
人是天生多妻主義的,人也是天生一夫一妻的。
这一炸,炸断了多少故事的尾巴。
玻璃窗上的手帕貼在那裏有許多天。
生在这世上,每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然而敦凤与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相爱着。踏着落花样的落叶一路行来,敦凤想着,经过邮局对面,不要忘了告诉他关于那鹦哥。
振保认识了一个名叫玫瑰的姑娘,因为这初恋,所以他把以后的两个女人都比作玫瑰。 也许她不过是个极平常的女孩子,不过因为年轻的缘故,有点什么地方使人不能懂得。
易太太笑道:“答应请客,赖不掉的。躲起来了。” 佳芝疑心马太太是吃醋,因为自从她来了,一切以她为中心。 “昨天是廖太太请客,这两天她一个人独赢,”易太太又告诉马太太。“碰见小李跟他太太,叫他们坐过来,小李说他们请的客还没到。我说廖太太请客难得 的,你们好意思不赏光?刚巧碰上小李大请客,来了一大桌子人。坐不下添椅子,还是挤不下,廖太太坐在我背后。我说还是我叫的条子漂亮!
我待她不错呀!我不爱她,可是我没有什么对不起她的地方。我待她不算坏了。下贱东西,大约她知道自己太不幸,必须找个比她再下贱的,来安慰她自己。可是我待她这么好,这么好——“ 他看着自己的皮肉,不像是自己在看,而像是自己之外的一个爱人,深深悲伤着,觉得他白糟蹋了自己。 像两扇紧闭的白门,两边阴阴点着灯,在旷野的夜晚,拼命的拍门,断定了门背后发生了谋杀案。然而把门打开了走进去,没有谋杀案,连房屋没有,只看见稀星下的一片荒烟蔓草——那真是可怕的。
如同一个含冤的小孩,哭着,不得下台,不知道怎样停止,声嘶力竭,也得继续哭下去,渐渐忘了起初是为什么哭的。
振保觉得她完全被打败了,得意之极,立在那里无声地笑着,静静的笑从他眼里流出来,像眼泪似的流了一脸。
大家算胡子,易先生乘乱里向佳芝把下颏朝门口略偏了偏。
“你们要看钻戒。坐下,坐下。”他慢吞吞腆着肚子走向屋隅,俯身去开一只古旧的绿毯面小矮保险箱。
易先生笑道:“你那只火油钻十几克拉,又不是鸽子蛋,‘钻石’墨,也是石头,戴在手上牌都打不动了。 牌桌上的确是戒指展览会,佳芝想。只有她没有钻戒,戴来戴去这只翡翠的,早知不戴了,叫人见笑——正眼都看不得她。 易太太道:“不买还要听你这些话!”说着打出一张五筒,马太太对面的黑斗篷啪啦摊下牌来,顿时一片笑叹怨尤声,方剪断话锋。
有时在公园里遇着了雨,长安撑起了伞,世舫为她擎着。隔着半透明的蓝绸伞,千万粒雨珠闪着光,像一天的星。一天的星到处跟着他们,在水珠银烂的车窗上,汽车驰过了红灯、绿灯,窗子外营营飞着一窠红的星,又是一窠绿的星?
只有现在,紧张得拉长到永恒的这一刹那间,这室内小一陽一台上一灯荧然,映衬着楼下门窗上一片白色的天光。有这印度人在旁边,只有更觉得是他们俩在灯下单独相对,又密切又拘束,还从来没有过。但是就连此刻她也再也不会想到她一爱一不一爱一他,而是—— 他不在看她,脸上的微笑有点悲哀。本来以为想不到中年以后还有这样的奇遇。当然也是权势的魔力。那倒还犹可,他的权力与他本人多少是分不开的。对女人,礼也是非送不可的,不过送早了就像是看不起她。明知是这么回事,不让他自我陶醉一下,不免怃然。
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振保对于烟鹂有许多不可告人的不满的地方,烟鹂因为不喜欢运动,连“最好的户内运动”也不喜欢。 ……对于一切渐渐习惯了之后,她变成了一个很乏味的妇人。 他心中留下了神圣而感伤的一角,放着这两个爱人。他记忆中的王娇蕊变得和玫瑰一而二二而一了,是一个痴心爱着他的天真热情的女孩子,没有头脑,没有一点使他不安的地方,而他,为了崇高的理智的制裁,以超人的铁一般的决定,舍弃了她。
有一天她看見那件咖啡色絨線衫高掛在宿舍走廊上晒太陽,認得那針織的壘的小葡萄花樣。四顧無人,她輕輕的拉著一只袖口,貼在面頰上,依戀了一會。有目的的愛都不是真愛,她想。那些到了戀愛結婚的年齡,為自己著想,或是為了家庭社會傳宗接代,那不是愛情。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想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流苏道:“你早就说过你爱我。” 柳原笑道,“那不算。我们那时候太忙着谈恋爱了,哪里还有工夫恋爱?” 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然而郭凤和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相爱的。 这世界上有那么许多人,可是他们不能陪你回家。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这世界上有那么许多人,可是他们不能陪着你回家。到了夜深人静,还有无论何时,只要生死关头,深的暗的所在,那时候只能有一个真心爱的妻,或者就是寂寞的。振保并没有分明地这样想着,只觉得一阵凄惶。
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一个好人。
炭起初是树木,后来死了,现在,身子里通过红隐隐的火,又活过来,然而,活着,就快成灰了。
到公共租界很有一截子路。三轮车踏到静安寺路西摩路口,她叫在路角一家小咖啡馆前停下。万一他的车先到,看看路边,只有再过去点停着个木炭汽车。 这家大概主要靠门市外卖,只装着寥寥几个卡位,虽然阴暗,情调毫无。靠里有个冷气玻璃柜台装着各色西点,后面一个狭小的甬道灯点得雪亮,照出里面的墙 壁下半截漆成咖啡色,亮晶晶的凸凹不平;一只小冰箱旁边挂着白号衣,上面近房顶成排挂着西崽脱换下来的线呢长夹袍,估衣铺一般。
她仿佛是个聪明直爽的人,虽然是为人妻了,精神上还是发育未完全的。 男人憧憬着一个女人的身体的时候,就关心到她的灵魂,自己骗自己说是爱上了她的灵魂。唯有占有她的身体之后,他才能忘记她的灵魂。也许这是唯一的解脱的方法。 这穿堂在暗黄的灯照里很像一截火车,从异乡开到异乡。火车上的女人是萍水相逢的,但是个可亲的女人。 真是个孩子,被惯坏了,一向要什么有什么,因此,遇见了一个略具抵抗力的,便觉得他是值得思念的。婴孩的头脑和成熟的妇人的美是最具诱惑性的联合。这下子振保完全被征服了。 车子轰轰然朝太阳驰去,朝他的快乐驰去,他的无耻的快乐——怎么不是无耻的?他这女人,吃着旁人的饭,住着旁人的房子,姓着旁人的姓。可是振保的快乐更为快乐,因为觉得不应该。
她立即瞥了两个黑斗篷一眼,还好,不像有人注意到。她赔出筹码,拿起茶杯来喝了一口,忽道:“该死我这记性!约了三点钟谈生意,会忘得干干净净。怎么办,易先生先替我打两圈,马上回来。” 易太太叫将起来道:“不行!哪有这样的?早又不说,不作兴的。” “我还正想着手风转了。”刚胡了一牌的黑斗篷呻吟着说。 “除非找廖太太来。去打个电话给廖太太。”易太太又向佳芝道:“等来了再走。” “易先生替我打着。”佳芝看了看手表。“已经晚了,约了个掮客吃咖啡。”
天就快亮了。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点,低一点,大一点,像赤金的脸盆,沉了下去。天是森冷的蟹壳青
……你年轻么?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这里,青春是不希罕的。他们有的是青春——孩子一个个的被生出来,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新的智慧。一年又一年的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这一代便被吸收到朱红洒金的辉煌的背景里去,一点一点的淡金便是从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
也许每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 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 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街上卖笛子的人在那里吹笛子,尖柔扭捏的东方的歌,一扭一扭出来了,像绣像小说插图里画的梦,一缕白气,从帐子里出来,胀大了,内中有种种幻境,像懒蛇一般地舒展开来,后来因为太瞌睡,终于连梦也睡着了。
人又不是貓狗,放一男一女在一間房裹就真會怎樣。
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他是不相信来生的,不然他化了名也要重来一趟。 普通人的一生,再好些也是“桃花扇”,撞破了头,血溅到扇子上,就这上面略加点染成为一枝桃花。振保的扇子却还是空白,而且笔酣墨饱,窗明几净,只等他落笔。
一灘灘的笑不停的從眼睛裏滿出來,必須狹窄了眼睛去合住它。她走到桌子前面,又向蠟燭說道:一宗豫!宗豫!一燭火因為她口中的氣而盪漾著了。
深夜的汽车道上,微风白雾,轻轻拍在脸上像个毛毛的粉扑子。车里的谈话也是轻飘飘的,标准英国式的,有一下没一下。玫瑰知道她已经失去他了。由于一种绝望的执拗,她从心底热出来。 车窗外还是那不着边际的轻风湿雾,虚飘飘叫人浑身气力没处用,只有用在拥抱上。玫瑰紧紧吊在他颈项上,老是觉得浑身不对劲,换一个姿势,又换一个姿势,不知道怎样贴得更紧一点才好。恨不得生在他身上,嵌在他身上。振保心里也乱了主意。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玫瑰爱他爱到这程度,他要怎样就怎样。
他不知道烟鹂听无线电,不过是愿意听见人的声音。 振保自从结婚以来,老觉得外界的一切人,从他母亲起,都应当拍拍他的肩膀奖励有加。像他母亲是知道他牺牲的详情的,即是那些不知底细的人,他也觉得人家欠着他一点敬意,一点温情的补偿。
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的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普通人向来是这样把节烈两个字分开来讲的。
牌桌上提起易太太替他买的好几套西装料子,预备先做两套。佳芝介绍一家服装店,是他们的熟裁缝。“不过现在是旺季,忙着做游客生意,能够一拖几个月,这样好了,易先生几时有空,易太太打个电话给我,我去带他来。老主顾了,他不好意思不赶一赶。”临走丢下她的电话号码,易先生乘他太太送她出去,一定会抄了去,过两天找个借口打电话来探探口气,在办公时间内,麦先生不在家的时候。 那天晚上微雨,黄磊开车接她回来,一同上楼,大家都在等信。一次空前成功的演出,下了台还没下装,自己都觉得顾盼间光艳一照人。她舍不得他们走,恨不得再到那里去。已经下半夜了,邝裕民他们又不跳舞,找那种通宵营业的小馆子去吃及第粥也好,在一毛一毛一雨里老远一路走回来,疯到天亮。
流苏道:“你早就说过你爱我。” 柳原笑道,“那不算。我们那时候太忙着谈恋爱了,哪里还有工夫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