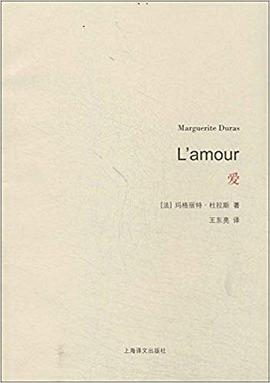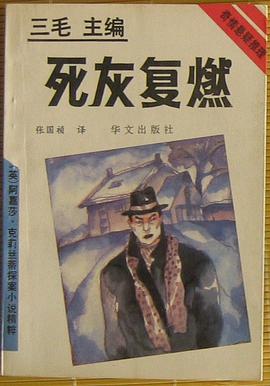内容简介
《活着》讲述一个人一生的故事,这是一个历尽世间沧桑和磨难老人的人生感言,是一幕演绎人生苦难经历的戏剧。小说的叙述者“我”在年轻时获得了一个游手好闲的职业——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在夏天刚刚来到的季节,遇到那位名叫福贵的老人,听他讲述了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 地主少爷福贵嗜赌成性,终于赌光了家业一贫如洗,穷困之中福贵因母亲生病前去求医,没想到半路上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后被解放军所俘虏,回到家乡他才知道母亲已经过世,妻子家珍含辛茹苦带大了一双儿女,但女儿不幸变成了哑巴。
真正的悲剧从此才开始渐次上演。家珍因患有软骨病而干不了重活;儿子因与县长夫人血型相同,为救县长夫人抽血过多而亡;女儿凤霞与队长介绍的城里的偏头二喜喜结良缘,产下一男婴后,因大出血死在手术台上;而凤霞死后三个月家珍也相继去世;二喜是搬运工,因吊车出了差错,被两排水泥板夹死;外孙苦根便随福贵回到乡下,生活十分艰难,就连豆子都很难吃上,福贵心疼便给苦根煮豆吃,不料苦根却因吃豆子撑死……生命里难得的温情将被一次次死亡撕扯得粉碎,只剩得老了的福贵伴随着一头老牛在阳光下回忆。
所获荣誉
这部小说荣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最高奖项(1998年),台湾《中国时报》十本好书奖(1994年),香港“博益”15本好书奖(1990年),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2004年),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2005年),法国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2008年);并入选香港《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百年百强”;入选中国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10部作品”。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
......(更多)
作者简介
余华,浙江海盐人,1960年出生于浙江杭州,后来随父母迁居海盐县。中学毕业后,因父母是医生,余华曾当过牙医,五年后弃医从文,进入县文化馆和嘉兴文联,从此开始文学创作生涯。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中文系合办的研究生班深造,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余华是中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与叶兆言、苏童等人齐名。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十八岁出门远行》、《世事如烟》,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战栗》及《兄弟》。
......(更多)
目录
......(更多)
读书文摘
出现在帕拉多眼前的是天堂。周围没有积雪。白色冰壳之下,灰色的水流倾泻而出,咆哮着涌进峡谷,撞击着巨石,一路向西奔去。更美的是,四下里青翠欲滴,苔藓、青草、灯心草、刺柏,还有黄色和紫色的野花。
“快!快跑!在河对岸!”卡涅萨用他尖利的嗓音大叫。帕拉多开始朝河边跑,卡涅萨也挣扎着爬过草地和石头,朝三四百码开外的骑马人挪动。……令人大失所望的是,当卡涅萨朝咆哮的激流对岸张望时,刚才看见骑马人的地方,却只有一块高耸的岩石和它投下的长长的影子。
“年轻时靠着祖上留下的钱风光了一阵子, 往后就越过越落魄了,这样反倒好,看看我身边的人,龙二和春生,他们也只是风光了一阵子, 到头来命都丢了。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 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 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 我还活着。”
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中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
鸡养大了变成鹅,鹅养大了变成羊,羊大了又变成牛。
生的终止不过一场死亡,死的意义不过在于重生或永眠。死亡不是失去生命,而是走出时间。
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
外人看来是悲剧,可当事人只拿它当一段人生。
生命中其实是没有幸福或者不幸的,生命只是活着,静静地活着,有一丝孤零零的意味。
生活和幸存就是一枚分币的两面,它们之间轻微的分界在于方向的不同。
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
活着,是一次残忍的阅读,余华不遗余力地展示误导的命运如何摧毁人的生活。
人死像熟透的梨,离树而落,梨者,离也。
人老了也是人,是人就得干净些。
活着什么也不为,就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
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
在文学的叙述里,没有什么比时间更具说服力了,因为时间无须通知什么就可以改变一切。
我沉湎于想象之中,又被现实紧紧控制,我明确感受着自我的分裂。
活着就是为了活着本身,而不是活着之外的的任何事物。
检验一个人的标准,就是看他把时间放在了哪儿。别自欺欺人;当生命走到尽头,只有时间不会撒谎。
人类无法忍受太多的真实。
人要是累得整天没力气,就不会去乱想了。
我们会来到这个世界,是不得不来;我们最终会离开这个世界,是不得不离开。
被命运碾压过,才懂时间的慈悲。
抬担架的都猫着腰,跑到我们近前找一块空地,喊一、二、三,喊到三时将担架一翻,倒垃圾似的将伤号扔到地上就不管了。
那件绸衣我往身上一穿就赶紧脱了下来,那个难受啊,滑溜溜的像是穿上了鼻涕做的衣服。
你的命是爹娘给的,你不要命了也得先去问问他们。
福贵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喜欢回想过去,喜欢讲述自己,似乎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一次一次地重度此生了。
可是我再也没遇到一个像福贵这样令我难忘的人了,对自己的经历如此清楚,又能如此精彩地讲述自己。他是那种能够看到自己过去模样的人,他可以准确地看到自己年轻时走路的姿态,甚至可以看到自己是如何衰老的。这样的老人在乡间实在难以遇上,也许是困苦的生活损坏了他们的记忆,面对往事他们通常显得木讷,常常以不知所措的微笑搪塞过去。他们对自己的经历缺乏热情,仿佛是道听途说般地只记得零星几点,即便是这零星几点也都是自身之外的记忆,用一、两句话表达了他们所认为的一切。
那时候最多的就是子弹了,往哪里躺都硌得身体疼。
人只要活得高兴,穷也不怕。
可是我再也没遇到一个像福贵这样令我难忘的人了,对自己的经历如此清楚,又能如此精彩地讲述自己是如何衰老的。这样的老人在乡间实在是难以遇上,也许是困苦的生活损坏了他们的记忆,面对往事他们通常显得木讷,常常以不知所措的微笑搪塞过去。
老子就是啃你家祖坟里的烂骨头,也不会向你要饭。
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什么福分了。
俗话说是笨鸟先飞,我还得笨鸟多飞。
你千万别糊涂,死人都还想活过来,你一个大活人可不能去死。
这钢铁能造三颗炮弹,全部打到台湾去,一颗打在蒋介石床上,一颗打在蒋介石吃饭的桌上,一颗打在蒋介石家的羊棚里。
女人都是一个心眼,她认准的事谁也不能让她变。
喂,你知道老良在哪里?死啦妈的,他还欠我一个银元呢
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他们对自己的经历缺乏热情,仿佛是道听途说般地只记得零星几点,即便是这零星几点也都是自身之外的记忆,用一、两句话表达了他们所认为的一切。
家珍是你的女人,不是别人的,谁也抢不走。
我知道他不会和我拼命了,可他说的话就像是一把钝刀子在割我的脖子,脑袋掉不下来,倒是疼得死去活来。
从前,我们徐家的老祖宗不过是养了一只鸡,鸡养大后变成了鹅,鹅养大了变成了羊,再把羊养大,羊就变成了牛。我们徐家就是这样发起来的。
女人啊,性子上来了什么事都干,什么话都说。
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这孩子也不做错事,让我发脾气都找不到地方。
最初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因为不得不来;最终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是因为不得不走。这中间的过程就随心的活着吧!
死亡不是失去了生命,只是走出了时间。
人的友爱和同情往往只是作为情绪来到,而相反的事实则是伸手便可触及。
他喜欢回想过去,喜欢讲述自己,似乎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一次一次的重度此生了。
人都是一样的,手伸进别人口袋里掏钱时那个眉开眼笑,轮到自己给钱了一个个都跟哭丧一样。
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
生活是一个人对自己经历的感受,而幸存往往是旁观者对别人经历的看法。
到了傍晚,我们两个人就坐在门槛上,看着太阳落下去,田野上红红一片闪着,听着村里人吆喝的声音,家里养着的两只母鸡在我们面前走来走去,苦根和我亲热,两个人坐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
做人不能忘记四条,话不要说错,床不要睡错,门槛不要踏错,口袋不要摸错。
活着是自己去感受活着的幸福和辛苦,无聊和平庸;幸存,不过是旁人的评价罢了。
我知道他不会和我拼命了,可他说的话就像是一把钝刀子在割我的脖子,脑袋掉不下来,倒是疼得死去活来。
人啊,活着时受了再多的苦,到了快死的时候也会想个法子来宽慰自己。
老人黝黑的脸在阳光里笑的十分生动,脸上的皱纹欢乐地游动着,里面镶满了泥土,就如布满田间的小道。
没有什么比时间更具有说服力了,因为时间无需通知我们就可以改变一切。
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
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
内心让他真实地了解自己,一旦了解了自己也就了解了世界。
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一个人命再大,要是自己想死,那就怎么也活不了。
凤霞、有庆都死在我前头,我心也定了,用不着再为他们操心,怎么说我也是做娘的女人,两个孩子活着时都孝顺我,做人能做成这样我该知足了。
对自己的经历如此清楚,又能如此精彩地讲述自己。他是那种能够看到自己过去模样的人,他可以准确地看到自己年轻时走路的姿态,甚至可以看到自己是如何衰老的。这样的老人在乡间实在难以遇上,也许是困苦的生活损坏了他们的记忆,面对往事他们通常显得木纳,常常以不知所措的微笑搪塞过去。他们对自己的经历缺乏热情,仿佛回到了道听途说般的只记得零星几点,即便是这零星几点也都是自生之外的记忆,用一两句话表达了他们所认为的一切。
作为一个词语,“ 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