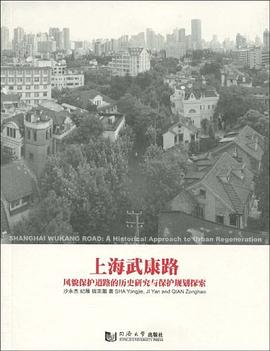里尔克法文诗
内容简介
在二十世纪的德语诗人中间,似乎还没有哪一位像本集的作者那样:童年寂寞而暗淡,一生无家可归,临终死得既痛苦又孤单,而在诗歌艺术的造诣上,却永生到放射着穿透时空的日益高远的光辉,就一些著名篇什的艺术纵深度而论,就其对心灵的撞击程度而论,真可称之为惊风雨而泣鬼神。诗人的全名是勒内·卡尔·威廉·约翰·约瑟夫·马利亚·里尔克;他本人的签名历来却只是:赖纳·马利亚·里尔克。
这里的法语诗对我们是既熟悉又陌生的,这是法语这种语言“精确性和抒情性完美结合”的最佳范本之一。
里尔克作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德语诗人的地位依然无可置疑,在他的诗作中,诗的纯美与哲学的深思的结合几近完美。他是喧嚣尘世中的一个孤独者,终身都在寻找精神的故乡。他的诗艺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善于把他所敏锐地感受和深入地思考的一切,都凝聚为精致而又独特的意象,如同雕塑一般展现在我们跟前。读他的诗,你无法不感到震撼,你会在恐惧中若有所思。
......(更多)
作者简介
(何家炜自传)
何家炜,1973年3月出生于浙江湖州,1996年毕业于广州外国语学院西语系法语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工作、游历、写诗、译诗,五六年如白驹过隙。
最初读里尔克是大学二年级,广州,1993年春天的一个美好的夜晚。那时广外有一个诗社,十四五个诗社成员,互相交流诗作和阅读,印刷简朴无比的诗刊。因为都是学外语的,也译介自己喜欢的外国诗歌,遗憾的是,诗社成员里没有学德语的。第一次接触里尔克,是同样是诗社成员的女友的推荐,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我们散步在校园林荫道清凉的路灯光下,她突然问我:“你读过里尔克的诗吗?”——这就是她抄在阅读笔记里的三首:一首是《豹》,一首是《秋日》,还有一首是《Pièta》,都是冯至的译笔。
自此后就开始阅读所有能找得到的里尔克的中文译本。由于自己的专业是法语,对里尔克的阅读从未离开中文的语境,但到大学三年级选修二外时,倒是想过修德语,但学校的规定是,所有非英语专业的学生,二外必须学英语。我没有读到德语中的里尔克,至今没有。德语班就在我们法语班隔壁,另一边是西班牙语班,那时广外西语系的学生中有句话:英语是说给商人听的,法语是说给情人听的,德语是说给上帝听的,而西班牙语是说给魔鬼听的。还有另一个版本,说:德语是说给敌人听的。我没有接触到这种似乎可以与上帝和敌人同时说话的语言,但我知道,法语也并非全是说给情人听的,因为那时我正沉迷于对法国象征派诗歌的阅读,而浸淫最深的则是写了《地狱一季》和《灵光集》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天才诗人阿瑟·兰波,以致毕业的时候,我的论文也是关于兰波的诗歌。
广外的阅读环境不是很好,图书馆和西语系的外文资料总是缺这少那的,但就在图书馆外文库的隔壁,有一间二十平米的小间,是梁宗岱先生的藏书陈列室。它是不对学生开放的,但是有一次,仅仅一次,为了给当时的《岭南文化时报》写一篇关于梁宗岱先生的文章——或者,应该倒过来讲——我进了梁老的藏书室。我现在想起这桩事,依然有一种欣奋而又肃然起敬的感情油然而生。我看到了一位诗人翻译家的繁复而奇妙的精神世界:线装的中国古诗轻无重量,各种外文书籍和辞典压得层层隔板好似摇摇欲坠,梁老的《晚祷》,瓦雷里签名的诗论集,1912年版的兰波全集,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梁老译的王维诗《酬张少府》草稿,……还有《本草纲目》等一些中草药的线装书。
在《梁宗岱译诗集》里,读到了《旗手的爱与死之歌》及《严重的时刻》等几首里尔克的短诗,还有歌德的《一切的顶峰》,布莱克的《天真的预示》,莎士比亚的《十四行》等等。梁老在莎士比亚的诗歌上花了太多心思,从我们今天的目光看,这许是一个失误。可能离开的时代太近,他对里尔克诗歌的关注远远不够,从今天看,对中国近代白话诗和现代新诗产生重要影响的外国诗人中,里尔克或许是首当其冲的一位。
也许是从那时起,我就萌生了翻译里尔克法文诗的念头。1994年的一天,我从我的外教Pierre Jeanne先生(中文名:任致远,是一位长年任教在中国的天主教士,学生间叫他绰号:老皮)那里借了一本很精美的法语文学读本,发现里面收了里尔克的三首法文诗,这让我有些欣喜若狂,这三首分别是《果园》第六首和第三十四首以及《玫瑰集》的第六首:
一朵玫瑰,就是所有的玫瑰
与她自身:这不可替代的
完美,这甜蜜的词汇
被事物的文本所包围。
如果没有她永不知如何说
我们的希望也无从依托,
在持续的出发程途,
途中又有温柔的间断。
这样的法语诗当时对我是既熟悉又陌生的。我曾经跟诗社的朋友说,这是法语这种语言“精确性和抒情性完美结合”的最佳范本之一。
但1996离开广外之后,我好几年没有接触到里尔克的法文诗,依然是这三首伴我在生活、工作、游历的年月里走来走去。直到有一天,2000年秋天,我在西非的一个海港小城Nouadhibou的一家当地摩尔人开的网吧里给远方的朋友写信,突然想起在网上寻找里尔克的法文诗,——
Ô nostalgie des lieux qui n'étaient point
assez aimés à l'heure passagère,
que je voudrais leur rendre de loin
le geste oublié, l'action supplémentaire!
Revenir sur mes pas, refaire doucement
- et cette fois, seul - tel voyage,
rester à la fontaine davantage,
toucher cet arbre, caresser ce banc...
哦,思念的是那些在匆匆而过的
时辰里没有被爱够的地方,
我真想从远处向它们奉还
遗忘的手势,这多余的行为!
重拾我的脚步——这次独自一人——
慢慢重塑这趟旅程,
在喷泉旁再多呆一会儿,
触摸这树枝,抚摩这坐凳……
当时我在电脑前读着这样的诗句,几乎热泪盈眶,——摩尔姑娘阿伊夏Aicha端给我一小杯滚烫的加薄荷的浓茶,——她说:这是来自中国的茶叶。我说:噢。
我背诵了这首诗,《果园》第四十一首。
就这样我重新开始读里尔克的法文诗。我不是做学问的人,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和精力去研究里尔克的诗。翻译他的诗是出于感动和敬佩,就像一位在美国写诗的朋友所言:He's great!
当然,对于里尔克这样一位影响中文诗歌创作的诗人,我充满了绍介的热情,以及自己想要从中学习诗歌这种语言艺术的愿望。但是,我对自己翻译诗歌的水平不敢高估。我能做的,就是尽我所能保持原文的面貌,不求如何传神如何流畅,只求让读者在阅读我的译文时,大致能想象到一些里尔克法文诗的魅力。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对自己的劳动还是满意的。
何家炜
2002年1月 青岛
......(更多)
目录
读书文摘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