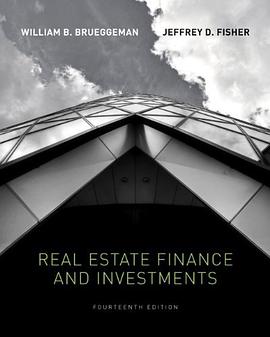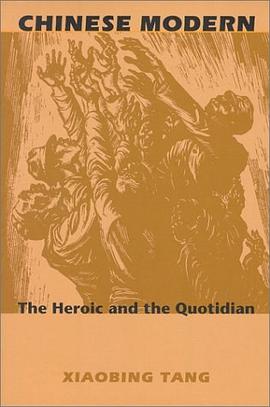罗贝尔·杜瓦诺
内容简介
假如巴黎是个剧场,罗贝尔•杜瓦诺则是有耐心的观众,不分昼夜地等待他的剧目上演,偶尔升格为导演。他与亨利•卡蒂埃-布雷松、布劳绍伊、欧仁•阿捷特并称法国四大摄影家,虽受布劳绍伊的影响,却有他独到的“法国人道关怀摄影”取向,而这些影像,不但是法国的重要文化资产,也是全世界的影像资产。
在法国摄影界,罗伯特·杜瓦诺和利·卡笛尔·布列松堪称为一对并驾齐驱的大师。这两人的摄影都以纪实为主,但风格却迥然不同。
布列松经常云游四海,作品比较深沉严肃,关心各地民族疾苦。杜瓦诺则一生只以他所居住的巴黎为创作基地,喜欢在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抓取幽默风趣的瞬间。
黑白摄影作品则引领我们攀上另一个高度,进入另一个时空,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在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我希望我们可以通过那些在那个时空和文化背景下,散发着时光气息的作品主题,了解罗伯特.杜瓦诺作品的精髓。
本书由Buclas·布克引进中国,这一经典将以“时间影集”的方式展现在中国读者的面前。这不仅仅是一本图书,一本优秀精美的摄影集,更是一本可以永久使用的万年历,一本祭奠时间的绝佳礼品、收藏品。
《时光与城市》
罗伯特.杜瓦诺的黑白作品让我忆起了照相暗盒这种最早期的摄影设备,人类早在金字塔时期就发现了光源乃一切影像之源的奥秘。
经过了漫长岁月,摄影才成为捕捉影像的一种方式,然后,再慢慢被视为一种表达手法。
随着赛璐珞胶卷面世,更现代化的照相机以其灵活可携的特点压倒了早期的影楼摄影。这项技术突破让摄影师可以随心所欲地去进行拍摄。而占据着罗伯特.杜瓦诺心田的,正是那个属于光与影的城市──巴黎。
在经典作品的殿堂里,我们经常欣赏到罗伯特.杜瓦诺、亨利.布列松、积赖恩.尼埃普斯、安塞尔.亚当斯和曼纽尔.布拉沃等摄影大师的黑白作品,这些跨时空之作,一直历久不衰。
事实上,时间于摄影而言,颇有点讽刺意味。时间是曝光度的指标,准确曝光是造就优秀作品的不可缺元素,但摄影又是一分半秒的凝结,是不起眼瞬间生活的捕捉,然后重现,让人细味。这就是摄影,一种受不同时间概念约束的艺术。
然而,本次摄影展令人惊喜之处,是可以带领大家从现今这个着重即时满足、全球交流的电子摄影年代,返回时光隧道不远处的那个时空,感受摄影师先用负片捕捉“阴”影像,然后再经显影转化成“正”影像,记录在相纸上一丝不苟的工艺流程,所有作品都是时间、耐心和技术的结晶。
如果说摄影技巧是成就一位出色摄影师的条件,那只可算是基本条件而已。罗伯特.杜瓦诺镜头中的巴黎不仅隐含了纯熟技巧,同时也蕴藏了作者对巴黎社会、人文和城市特征的深刻了解。
文化,是人类生存与交流的的载体,蕴含了所有艺术表达方式和生活形式,因此,了解文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罗伯特.杜瓦诺把城市,尤其是他喜爱的巴黎市,理解为一个活生生的载体,一个与城市及其居民的互动,一段文化古迹与孩童、子孙和城市设计师之间的对话。
参观“逝水年华──罗伯特.杜瓦诺摄影展”,犹如进入了时光旅程,一个我们久违了、没有色彩的视觉旅程。
然而,正是缺少了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色彩,才让这次展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大放异彩。
我们活在一个彩色世界,颜色过分直接地反映了我们感官的一切。
但黑白摄影作品则引领我们攀上另一个感官高度,进入另一个时空,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在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我希望我们可以通过那些在那个时空和文化背景下,散发着时光气息的作品主题,了解罗伯特.杜瓦诺作品的精髓。
如果做到了,如果能够与相片展开对话,我们就可以透过罗伯特.杜瓦诺的双眼,返回那个时空,探索巴黎独特的文化。这就是交流,需要的只是一位参与这次摄影展旅程的游人,简单至此而已。
......(更多)
作者简介
罗贝尔·杜瓦诺
——法国人道关怀摄影的代表
罗贝尔·杜瓦诺(1912~1994)是20世纪40~60年代“法国人道关怀摄影”巅峰期的代表人物,其作品以幽默而略带讽刺的日常生活取像著称。他是个地道的法国摄影家,终其一生对法国,特别是巴黎情有独钟,为世人留下超过40万张珍贵的巴黎影像。
法国人道关怀摄影
与美国人道关怀摄影(尤其族群的社会性议题)和马格南摄影通讯社的人道关怀摄影(全人类议题为主)不同,“法国人道关怀摄影”以维护法国人文与文化为本,在摄影史上自成一家:二战后,“法国人道关怀摄影”从广义的“人道关怀摄影”中抽离,以法国本位主义而与“马格南摄影通讯社”有所区别,彰显法国人不为战事所影响的尊贵气质与文化传承。
1947年,因不愿离开法国,不愿离开钟爱的出生地巴黎,罗贝尔·杜瓦诺毅然拒绝“马格南摄影通讯社”邀请,执意留在“Rapho摄影通讯社”与“XV俱乐部”。比起其他“法国人道关怀摄影家”,如布劳绍伊、维利·罗尼、伊吉斯、爱德华·布巴等,罗贝尔·杜瓦诺少了几分感性,而以适度的神圣、怀旧、诗意点缀其狡黠的玩笑。
其早期作品《两兄弟》,表现在巴黎街头倒立行走的两兄弟,另有两兄弟在旁羡慕观望;倒立走的两兄弟以姿态胆识造势,而瞠目结舌的两兄弟则衣着端庄华贵,其对比间不失诙谐。在满是古董艺术品店的巴黎第六区,罗贝尔·杜瓦诺躲在罗米艺廊橱窗后,拍下一系列巴黎人的真表情:在保守的上世纪40年代,俏女郎的裸臀画像并未摆在店面前方,而是位于人行道反向的一侧,但仍引起不少关注;最经典的一张《斜视》以反差取胜,在夫妻两人的反差神态中,制造了双重笑点——正当太太认真谈论眼前作品时,她的先生竟偏过头斜睨美女画像。
从1945年到1960年称罗贝尔·杜瓦诺的主要创作期,尤其50年代,有《地狱之门》《市府前的一吻》《做白日梦的男人》《脑瓜子》《桥上的猎狐狗与画家》《巴尔先生的旋转木马》《艾博广场的孩子们》及文化界人像摄影等名作。《地狱之门》超现实式地“咬住”路过的警员,这位不知情的警员还不悦地看着相机;在《桥上的猎狐狗与画家》里,猎狐狗的主人保持距离观看画家作画,而猎狐狗却好奇地正视镜头——在摄影艺术还混沌不明的年代,摄影者本人有意将摄影与绘画对照,此作在内容与题意上表现绘画的世俗地位。
罗贝尔·杜瓦诺对郊区中下阶层平民的生活亦多着墨:在混乱、贫困、移民充斥的巴黎第18区,一个姐姐拉住想靠近相机的妹妹;小女孩显然从未见过照相机,大男孩则以典型的法国人的优雅神态置身事外,这一切构成《艾伯广场的孩子们》真实却略为抽象的影像。继1949年的《巴黎郊区》、1954年《如此的巴黎人》摄影集后,1956年罗贝尔·杜瓦诺出版了《片刻巴黎》摄影集并在法国人道关怀摄影的巅峰期两度获得“尼尔普斯奖”(法国人尼尔普斯乃摄影术发现者)。
从60年代起,法国人道关怀摄影逐渐退出影像舞台,而罗贝尔·杜瓦诺却依然故我,漫步于巴黎的每条街道、每块石砖,发现每个令人惊喜的片段。在其晚期作品中,嘲讽与隐喻不时出入,趣味盎然,见证了巴黎逐渐后现代化的过程:《被掌控的维纳斯》在杜勒丽花园的重整中被两个搬运工掌握摆布;在17区的Morceau公园里闲逸休息的雕像与远方的小孩形成对应,此即《三个白衣小孩》;《直升机》以布满鸟粪的铜像对应空中盘旋的4架直升机(却不见鸽子或其他鸟);而《桥上的读书人》则在高楼林立的古桥上边走边读。
《市府前的一吻》
对罗贝尔·杜瓦诺来说,巴黎的价值不因时间而改变,巴黎风采依旧——尽管有时并不那么真实。他最知名的代表作《市府前的一吻》即一例。在50年,受托于美国《生活》杂志,罗贝尔·杜瓦诺制作了《巴黎的情侣》主题摄影,赋形巴黎为一浪漫城市;其中《市府前的一吻》成为巴黎的象征,红遍海内外并于80年代卖出50万张海报、250万张明信片及各种产品。但到1993年即其40多年后,当年的影像主角突然现身,索求40万法郎的肖像权费并将此事闹上法庭。昔日的女主角弗朗索瓦丝·布瓦内败诉之余,也揭发罗贝尔·杜瓦诺非纪实性拍摄的事实——在一个不太开放的年代,浪漫的巴黎并非处处可见拥吻场景,罗贝尔·杜瓦诺于是雇用弗朗西斯与其男友成就此情此景。
然而,在罗贝尔·杜瓦诺“认罪”后,这张照片更加值钱。2005年,弗朗索瓦丝·布瓦内将她手边当初用以作为报酬的那张照片交给拍卖会并以24.2万美元出售——罗贝尔·杜瓦诺的摄影大多数版数不明,初版照片更是罕见,因此虽此照片并非“初版”,却是“拍摄同期印出”的照片,价值不菲亦在情理。
时至21世纪,《市府前的一吻》并未因戏剧性的纷扰而改变,它无损于罗贝尔·杜瓦诺的创作价值,表现了巴黎的浪漫,其意义早已超过真相本身。
人像照作品
摄影艺术的价值并不由纪实或编导性的拍摄方式决定,尤其80年代“编导摄影”大行其道后,经编排、摆饰、有剧本的导演拍摄方式的锋芒已盖过“纪实摄影”。
但平心而论,罗贝尔·杜瓦诺的编导拍摄确实可圈可点,他的人像作品更不得错过。从40年代起,罗贝尔·杜瓦诺穿梭巴黎街头的同时,也进入巴黎文艺鼎盛的咖啡馆,拍下萨特、西蒙娜·波伏娃、阿尔贝托·贾科梅蒂等人流连其间的一幕;他还为毕加索、费尔南·莱热、科莱特、让·丁格利、罗贝尔·卡皮亚于居家、室外或工作室留影,创意兼具超现实主义与剧场型态。1944年,他拍女性主义哲学家西蒙娜·波伏娃在Deux Margots咖啡馆专心写作;1952年,他来到毕加索位于法国南部的家,拍了一系列毕加索居家照片:《毕加索的面包手》成为经典,而毕加索双手贴住窗户的那张照片则登上《生活》杂志封面——真实生活中,毕加索的双手确实又圆又大且指节圆胖,所以在《毕加索的面包手》影像里,他神情严肃,没有作怪,反而让人发笑。1954年,罗贝尔·杜瓦诺在莱热工作室置莱热于交迭的画作间,在莱热指针性的人与符号的图案间,几乎看不到他的存在。而1959年,罗贝尔·杜瓦诺则拍下让·丁格利被自己的烟雾作品罩住脸的瞬间。1976年的某晚,罗贝尔·杜瓦诺还隔着一条街,水平拍摄了自家窗台上的演员罗贝尔·卡皮亚;影像里,主角罗贝尔·卡皮亚不但没有居中还被缩小成远景的一部分,楼下别致的商店橱窗与步行道成为主体,“人”则是巴黎精致格调中的小部分。
假如巴黎是个剧场,罗贝尔·杜瓦诺则是有耐心的观众,不分昼夜地等待他的剧目上演,偶尔升格为导演。他与亨利·卡蒂埃-布雷松、布劳绍伊、欧仁·阿捷特并称法国四大摄影家,虽受布劳绍伊的影响,却有他独到的“法国人道关怀摄影”取向,而这些影像,不但是法国的重要文化资产,也是全世界的影像资产。
......(更多)
目录
读书文摘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