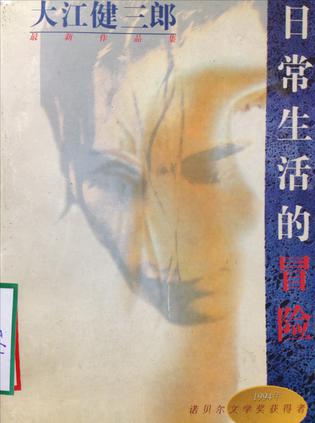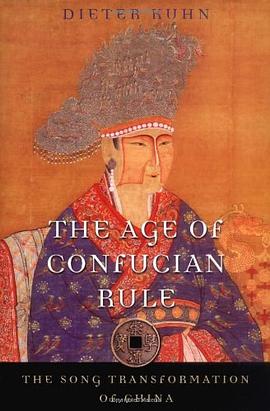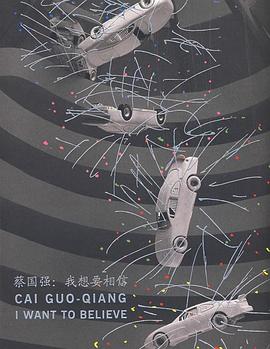内容简介
......(更多)
作者简介
大江健三郎生平
大江健三郎(1935年—— ),日本著名文学家。
1935年1月31日,大江健三郎出生于日本四国岛的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在七兄弟中排行老三。1941年入大濑国民学校就读,1944年丧父。战争结束后,大江健三郎于1947年进入战后设立的新制中学——大濑中学接受民主主义教育,并以同年5月颁布的新宪法作为自己的道德规范。1950年入县立内子高中,翌年转入县立松山东高中,在校期间编辑学生文艺杂志《掌上》。1953年高中毕业后大江健三郎赴东京,入补习学校做报考大学的准备。1954年考入东京大学文科,热衷于阅读加缪、萨特、福克纳和安部公房等人的作品。1955年入东京大学法文专业,在渡边一夫教授的影响下开始阅读萨特的法文原作,并创作剧本《死人无口》和《野兽们的声音》。大江健三郎积极从事文学活动,于1957年5月在《东京大学新闻》上发表《奇妙的工作》并获该报“五月祭奖”。著名文艺评论家平野谦在《文艺、时评》上谈到该短篇小说时,认为这是一篇“具有现代意识的艺术作品”。在这一年里,大江健三郎还相继发表了习作《死者的奢华》、《人羊》和《他人的脚》等短篇小说,其中《死者的奢华》被荐为芥川奖候选作品,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称赞该作品显现出作者“异常的才能”。自此,大江健三郎作为学生作家开始崭露头角。1958年又发表了《饲育》和《在看之前便跳》等短篇小说,其中《饲育》获得第39届芥川奖,使得这位学生作家得以与石原慎太郎、开高健和江藤淳等人齐名,同被视为文学新时期的象征和代表;而稍后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摘嫩菜打孩子》,则更是决定性地把他放在了新文学旗手的位置上。
1959年3月,大江健三郎完成学业,从东京大学法文专业毕业,其毕业论文为《论萨特小说里的形象》。同年,作者接连发表了长篇小说《我们的时代》和随笔《我们的性的世界》等作品,开始从性意识的角度来观察人生,试图表现都市青年封闭的内心世界。当时,这种尝试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作者也受到了种种攻击性批评。1960年2月,大江健三郎与著名电影导演伊丹万作的长女伊丹缘结婚,积极参加“安保批判之会”和“青年日本之会”的活动,明确表示反对日本与美国缔结安全保障条约,并因此而与石原慎太郎和江藤淳等人严重对立。在这一年里,大江健三郎还发表了长篇小说《青年的污名》,虚构性自传体长篇小说《迟到的青年》也于9月开始在《新潮》杂志连载。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具有较浓厚的民主主义色彩,反映出作者对社会和人生的思索。
出现在这一时期作品中的民主主义思想并不是偶然和孤立的。据作家本人回忆,他12岁时正逢日本公布新宪法,他认为宪法中“主权在民,放弃战争”的内容对他的思想形成具有很大影响。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和日本政府大规模整肃共产党员的事件,使得这位15岁的少年为理想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感到苦闷。 1960年5月底,在日本国内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的高潮中,这位已在日本文坛小有名气的战后派青年作家,参加了以野间宏为团长的第三次日本文学家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在中国进行访问的半个多月里,大江健三郎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先后受到了毛泽东、陈毅、郭沫若和茅盾等人的接见,大江健三郎本人还在《世界文学》杂志发表特约文章,认为日本人民在反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中“报答了中国人民的友谊,从而结成了永恒的友谊”,并且充满热情地写道:“我们日本人民向中国人民保证并发誓决不背叛你们,永远和你们保持友谊,从而恢复我们作为一个东方国家的日本人民的荣誉。”
二、大江健三郎的文学历程:
大江健三郎的这些经历,很难不对他的创作生涯产生影响。早在1958年,这位东京大学法文专业的学生作家在以小说《饲育》获芥川奖后即对报界表示:“我毫不怀疑通过文学可以参与政治。就这一意义而言,我很清楚自己之所以选择文学的责任。”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进一步谈及文学的责任时,这位作家认为:“所谓文学的责任,就是对20世纪所发生过的事和所做过的事进行总清算。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南京大屠杀、原子弹爆炸等对人类的文化和文明带来的影响,应给予明确的回答,并由此引导青年走向 21世纪。”1961年,他以右翼少年刺杀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事件为题材,写了《十七岁》和《政治少年之死》两部小说,通过对17岁少年沦为暗杀凶手的描写,揭露了天皇制的政治制度。《政治少年之死》在《文艺春秋》杂志发表后,大江健三郎立即遭到右翼势力的威胁,而《文艺春秋》杂志则未经作者本人同意,便刊登了道歉声明。自此,这篇小说再也未能收入到他的任何作品集里。
对于大江健三郎的创作生涯来说,1963年是个非常重要的年头。在这一年里,他的长子大江光出世了。这原本应该是一件喜事,却给这位28岁的青年作家蒙上了厚厚的阴影——婴儿的头盖骨先天异常,脑组织外溢,虽经治疗免于夭折,却留下了无法治愈的后遗症。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大江健三郎还去广岛参加了原子弹在广岛爆炸的有关调查,走访了许多爆炸中的幸存者。这两件与死亡相关联的事给这位作家带来了难以言喻的苦恼和极为强烈的震撼,使他把小的“死”(残疾病儿大江光的死的威胁)与大的“死”(全人类所面临的核武器爆炸的死的威胁)联系在一起,认为死亡的危险正经常性地显露出来。这种思考又使得作者在生活中不得不时时意识到死亡,并且将这种生活态度自觉不自觉地与自己的文学创作结合起来。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个人的体验》(1964年),正是作者在这种苦闷之中创作的一部以自身经历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如同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平野谦所盛赞的那样,“在大江健三郎至今的所有作品里,这是最为出色的一部”。在这部发表后即获得新潮文学奖的作品中,当主人公鸟在面临脑残疾婴儿的生死抉择——或听从情妇劝告,借黑市堕胎医生之手埋掉病儿,或接受医院建议,为病儿施行脑疝气手术以拯救其生命——时,最终决定听从医生的建议。这也就意味着,自己要同将会留下严重脑残疾的儿子共度生涯,从而把个人的不幸升华为人类的不幸。同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另一部作品《万延元年的足球队》(1967年)也属于这一类表现残疾人题材的长篇小说。在这部被称之为现代传奇小说的作品中,白痴儿的父亲蜜三郎与从美国回来的弟弟鹰四,一起返回故乡四国的群山之间,卖掉了百年老屋并寻找这座老屋所象征的祖先的谱系。早在万延元年(1860年)的农民起义中,他们的曾祖父(身为村长的老屋主人)与其任义军首领的弟弟相互对抗,最后曾祖父杀死了纵火焚烧老屋的弟弟。为把村里年轻人组织起来同朝鲜人抗衡,鹰四用卖老屋的钱办起一支足球队,蜜三郎却通过此事从鹰四身上看到了曾祖父弟弟的暴力基因。在计划抢劫朝鲜人的超级市场失败后,鹰四承认了奸污白痴妹妹并在致其怀孕后逼迫她自杀的事实,随后自己也用猎枪自杀身亡。蜜三郎与妻子商定,要把白痴儿子接回来,并收养鹰四的孩子。在整部作品里,作者以故乡四国的群山、森林和山村为舞台,把虚构与现实、过去与现在、畸形儿、暴动、通奸、乱伦和自杀交织在一起,勾画出一幅幅离奇的画面,并借该作品表现出自己的焦虑:人类应如何走出那片象征着核时代的恐怖和不安的“森林”。与前一时期的作品相比,作者在1963年以后发表的作品大多以残疾人和核问题为主要题材,具有较浓厚的人道主义倾向。就其艺术特色而言,在更成熟地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的同时,充分运用日本文学传统中的想象,把现实与虚构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还有《日常生活的冒险》(1964年)、《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1968年)、《洪水淹没我的灵魂》(1968年)等长篇小说。此外,大江健三郎在随笔和文学评论领域也非常活跃,著有《广岛日记》(1965年)、《作为同时代的人》(1973年)和《小说方法》(1978年)等作品和文论。
三、大江健三郎授奖情况:
授 奖
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埃斯普马克在授奖辞中指出:“核武器的悲惨后果是与脑功能障碍的儿子问题自然相关的另一个主题。大江通过萨特的存在主义获得的哲学要素——人生的悖谬、无可逃脱的责任、人的尊严——贯彻其作品始终,形成了大江文学的一个特征。……大江说他的眼睛并没有盯着世界的听众,只是在对日本的读者说话。但是,他的作品中却存在着‘变异的现实主义’这种超越语言与文化的契机、全新的见解和充满凝练形象的诗。使他回归自我主题的强烈迷恋消除了 (语言等)障碍。我们终于对作品中的人物感到亲切,对其变化感到惊讶,理解了作者有关真实与肉眼所见的一切均毫无价值这一见解。但价值存在于另外的层次,往往从众多变相的人和事物中最终产生纯人文主义的理想形象,我们大家全都关注的感人形象。”
受奖演说
1994年12月7日,大江健三郎在斯德哥尔摩瑞典皇家文学院发表了题为“我在暧昧的日本”(直译应为《暧昧的日本的我》。因受奖辞中多处借此标题进行对比说明,为便于理解,除标题外,其他各处均直译为“暧昧的日本的我”)的演讲,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文艺理念和文学主张。
大江说,第一个站在这里的日语作家川端康成,曾在此发表过题为《美丽的日本的我》的讲演。这一讲演极为美丽,同时也极为暧昧。这里使用的英语单词 vague,即相当于日语中“暧昧的”这一形容词。川端或许有意识地选择了“暧昧”,并且预先用讲演的标题来进行提示。这是通过日语中“美丽的日本的”里 “的”这个助词的功能来体现的。以“暧昧”这个词为起点,大江的受奖辞着力描述了自己所生存的世界《日本》的文化处境和自己独特的文学观的关联。
“倘若可能,为了我国的文明,为了不是因为文学和哲学,而是通过电子工程学和汽车生产工艺学而为世界所知的我国的文明,我希望能够起到叶芝的作用。在并不遥远的过去,那种破坏性的盲信,曾践踏了国内和周边国家的人民的理智。而我,则是拥有这种历史的国家的一位国民。”
“作为生活于现在这种时代的人,作为被这样的历史打上痛苦烙印的回忆者,我无法和川端一同喊出‘美丽的日本的我’。刚才,在谈论川端的暧昧时,我使用了 vague这一英语单词,现在我仍然要遵从英语圈的大诗人凯思琳·雷恩所下的定义——‘是ambiguous,而不是vague’,希望把日语中相同的暧昧译成ambiguous。因为,在谈论到自己时,我只能用‘暧昧的日本的我’来表达。”
受奖辞认为,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一百二十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ambiguity)的两极之间。而大江自己,身为被刻上子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
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在坚定、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了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就日本现代文学而言,那些最为自觉和诚实的“战后文学者”,即在那场大战后背负着战争创伤、同时也在渴望新生的作家群,力图填平与西欧先进国家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诸国间的深深沟壑。而在亚洲地区,他们则对日本军队的非人行为做了痛苦的赎罪,并以此为基础,从内心深处祈求和解。大江则志愿站在了表现出这种姿态的作家们的行列的最末尾,直至今日。
现代日本无论作为国家或是个人的现状,都孕育着双重性。以大约五十年前的战败为契机,正如“战后文学者”作为当事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日本和日本人在极其悲惨和痛苦的境况中又重新出发了。支撑着日本人走向新生的,是民主主义和放弃战争的誓言,这也是新的日本人最根本的道德观念。然而,蕴涵着这种道德观念的个人和社会,却并不是纯洁和清白的。作为曾践踏了亚洲的侵略者,他们染上了历史的污垢。而且,遭受了人类第一次核攻击的广岛和长崎的那些死者们,那些染上了放射病的幸存者们,那些从父母处遗传了这种放射病的第二代的患者们(除了日本人,还包括众多以朝鲜语为母语的不幸者),也在不断地审视着我们的道德观念。
西欧有着悠久传统——对那些拒绝服兵役者,人们会在良心上持宽容的态度。在那里,这种放弃战争的选择,难道不正是一种最容易理解的思想吗?如果把这种放弃战争的誓言从日本国的宪法中删去——为达到这一目的的策动,在国内时有发生,其中不乏试图利用国际上的所谓外来压力的策动——无疑将是对亚洲和广岛、长崎的牺牲者们最彻底的背叛。身为小说家,大江不得不想象,在这之后,还会接二连三地发生何种残忍的新的背叛。
支撑着现有宪法的市民感情超越了民主主义原理,把绝对价值置于更高的位置。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民主主义宪法下,与其说这种情感值得感怀,不如说它更为现实地存续了下来。假如日本人再次将另一种原理制度化,用以取代战后重新生发的道德规范,那么,我们为在崩溃了的现代化废墟上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而进行的祈祷,也就只能变得徒劳无益了。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的极其繁荣——尽管从世界经济的构想和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这种繁荣正孕育着种种危险的胎芽——使得日本人在近、现代化进程中培育出的慢性病一般的暧昧急剧膨胀,并呈现出更加新异的形态。关于这一点,国际间的批评之眼所看到的,远比我们在国内所感觉到的更为清晰。如同在战后忍受着赤贫,没有失去走向复兴的希望那样,日本人现在正从异常的繁荣下竭力挺起身子,忍受着对前途的巨大担忧,尽管这种说法有些奇妙。我们可以认为,日本的繁荣,有赖于亚洲经济领域内的生产和消费这两股潜在势力的增加,这种繁荣正不断呈现出新的形态。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所希望创作的严肃文学,与反映东京泛滥的消费文化和世界性从属文化的小说大相径庭,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界定我们日本人自身呢?
为了界定理想的日本人形象,大江试图从乔治·奥威尔时常使用的形容词中挑选“正派的”一词。奥威尔常用这词以及诸如“仁慈的”、“明智的”、“整洁的”等词来形容自己特别喜爱的人物形象。这些使人误以为十分简单的形容词,完全可以衬托大江在“暧昧的日本的我”这一句子中所使用的“暧昧”一词,并与它形成鲜明的对照。从外部所看到的日本人形象,与日本人所希望呈现的形象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
“倘若我将‘正派的’的人这一日本人的形象,与法语中‘人道主义者’的日本人这一表现重叠起来使用的话,我希望奥威尔不会提出异议,因为这两个词都含有宽容和人性之义。”
接着,大江的受奖辞谈到了自己的恩师,日本的法国文学专家、评论家渡边一夫。在大战爆发前夕和激烈进行时期的那种爱国狂热里,渡边尽管独自苦恼,却仍梦想着要将人文主义者的人际观,融入到自己未曾舍弃的日本传统审美意识和自然观中去,这是不同于川端的“美丽的日本”的另一种观念。
与其他国家为实现近、现代化而不顾一切的做法不同,日本的知识分子以一种相互影响的复杂方法,试图在很深的程度上把西欧同他们的岛国连接起来。这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劳作,却也充满了喜悦。尤其是渡边一夫所进行的弗朗索瓦·拉伯雷研究,更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我是渡边一夫在人生和文学方面的弟子。从渡边那里,我以两种形式接受了决定性的影响。其一是小说。在渡边有关拉伯雷的译著中,我具体学习和体验了米哈伊尔·巴赫金所提出并理论化了的‘荒诞现实主义或大众笑文化的形象系统’——物质性和肉体性原理的重要程度;宇宙性、社会性、肉体性等诸要素的紧密结合;死亡与再生情结的重合;还有公然推翻上下关系所引起的哄笑。”
“正是这些形象系统,使我得以植根于我周围的日本乃至周围的土地,同时开拓出一条到达和表现普遍性的道路。不久后,这些系统还把我同韩国的金芝河、中国的郑义和莫言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的基础,是亚洲这块土地上一直存续着的某种暗示——自古以来就似曾相识的感觉。当然,我所说的亚洲,并不是作为新兴经济势力而受到宠爱的亚洲,而是蕴含着持久的贫困和混沌的富庶的亚洲。在我看来,文学的世界性,首先应该建立在这种具体的联系之中。”
“渡边给予我的另一个影响,是人文主义思想。我把与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小说的精神’相重复的欧洲精神,作为一个有生气的整体接受了下来。像是要团团围住拉伯雷一般,渡边还写了易于读解的史料性评传。他的评传涵盖了伊拉斯谟和塞巴斯齐昂·卡斯泰利勇等人文学者,甚至还包括从围绕着亨利四世的玛尔戈王后到伽布利埃尔·黛托莱的诸多女性。就这样,渡边向日本人介绍了最具人性的人文主义,尤其是宽容的宝贵、人类的信仰、以及人类易于成为自己制造的机械的奴隶等观念。”
“他勤奋努力,传播了丹麦伟大语法学家克利斯托夫·尼罗普的名言‘不抗议(战争)的人,则是同谋者’,使之成为时事性的警句。渡边一夫通过把人文主义这种包孕着诸多思想的西欧母胎移植到日本,而大胆尝试了‘前所未闻的企图’,确实是一位‘庞大固埃(拉伯雷《巨人传》中的巨人王)式的、了不起的企图’的人。”
作为渡边的人文主义的弟子,大江希望通过自己这份小说家的工作,能使那些用语言进行表达的人及其接受者,从个人和时代的痛苦中共同恢复过来,并使他们各自心灵上的创伤得到医治。“我刚才说过被日本人的暧昧‘撕裂开来’这句话,因而我在文学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力图医治和恢复这些痛苦和刨伤。这种工作也是对共同拥有日语的同胞和朋友们确定相同方向而作的祈祷。”
四、评论界对大江健三郎获诺贝尔奖的反应:
大江对传统文化十分执著和尊重,从本民族的土壤中充分汲取营养,很好地继承并大量使用了自《竹取物语》(859—877年间)延续下来的象征性技法和日本文学传统中的想象力。与此同时,这位战后成长起来的作家异常热情地借鉴外来文化,并在充分消化的基础上予以吸收,显现出一种“冲突·并存·融合”的文化模式,使得自己的创作活动不仅面向日本和东方,同时也面对世界和现代。在谈到授奖原因时,瑞典文学院认为,大江氏在其作品中“通过诗意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把现实和神话紧密凝缩在一起的想象世界,描绘出了现代的芸芸众生相,给人们带来了冲击”。作者在把现实引入小说的同时,致力于非现实性的虚构(即日本文学传统中的玄虚),两者之间既截然分明,又随意重叠,而将这两者巧妙结合起来的,则是大江氏从日本文学传统中继承下来、又具有浓郁个人特色的象征性表现手法 (即日本文学传统中的幽玄)。在这个独特、丰富的想象世界里,出生于森林之中的大江氏似乎对森林情有独钟,在诸多以森林为舞台的小说中,大量导入日本文学传统中的想象力和日本神话的象征性,意在把现实中的神话意义剥离出来,好像在有意印证英国诗人布莱克的论点——出自森林的是生命,回归森林的则是完成了的死亡。其实,这是作者在人为地拉开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用虚构这一形式来表现和渲染潜于表层之下的现实。
出处:
......(更多)
目录
......(更多)
读书文摘
“不,他肯定知道要去哪里,只是时代不同了,现在有公共汽车、火车,还有飞机,和过去旅行者的情况不同了。俺那个年代的人去什么远处,只要离开家步行上路就是了。只要上路,肯定能到其他什么地方,走不了就让人背着走,遇到大海就坐轮船。俺那个年代的人,说走就走。没走的人每天看着自家门前的街道忍耐着。明治时代就是这么个光景!”
当然,他的微笑彻头彻尾是为他自己的,即使在与情人接吻时,他也为自己微笑。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