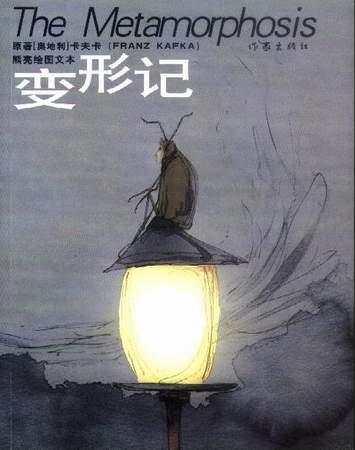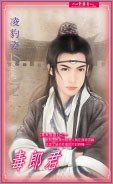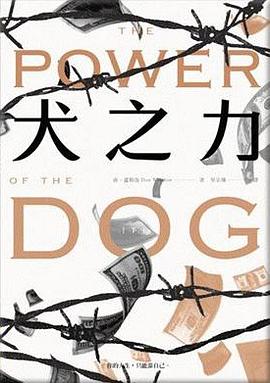内容简介
《变形记》的主要内容是:卡夫卡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山祖师,《变形记》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如果你想了解现代主义文学,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反复阅读《变形记》开始。在《变形记》中卡夫卡描述了小职员格里高尔•萨姆沙突然变成一只使家人都厌恶的大甲虫的荒诞情节,借以揭示人与人之间——包括伦常之间——表面上亲亲热热,内心里却极为孤独和陌生的实质,生动而深刻地再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在荒诞的、不合逻辑的世界里描绘"人类生活的一切活动及其逼真的细节",这正是著名小说家卡夫卡的天赋之所在。
......(更多)
作者简介
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
在西方现代文学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他生前在德语文坛上几乎鲜为人知,但死后却引起了世人广泛的注意,成为美学上、哲学上、宗教和社会观念上激烈争论的焦点,被誉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论年龄和创作年代,卡夫卡属于表现主义派一代,但他并没有认同于表现主义。他生活在布拉格德语文学的孤岛上,对歌德、克莱斯特、福楼拜、阳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托马斯・曼等名家的作品怀有浓厚的兴趣。在特殊的文学氛围里,卡夫卡不断吸收,不断融化,形成了独特的“卡夫卡风格”。他作品中别具一格甚至捉摸不透的东西就是那深深地蕴含于简单平淡的语言之中的、多层次交织的艺术结构。他的一生、他的环境和他的文学偏爱全都网织进那“永恒的谜”里。他几乎用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眼睛去看世界,在观察自我,在怀疑自身的价值,因此他的现实观和艺术现显得更加复杂,更加深邃,甚至神秘莫测。
布拉格是卡夫卡的诞生地,他在这里几乎度过了一生。到了生命最后的日子,他移居到柏林,试图摆脱不再是卡夫卡的布拉格。不管怎样,跟他的同胞里尔克和韦尔弗相比,卡夫卡与布拉格保持着更长时间和更密切的联系。在这个融汇着捷克、德意志、奥地利和犹太文化的布拉格,卡夫卡发现了他终身无法脱身的迷宫,永远也无法摆脱的命运。
......(更多)
目录
......(更多)
读书文摘
“起床这么早,”他想,“会使人变傻的。人是需要睡觉的。
他的背成了钢甲式的硬壳,他略一抬头,看见了他的拱形的棕色的肚皮。肚皮僵硬,呈弓形,并被分割成许多连在一起的小块。肚皮的高阜之处形成了一种全方位的下滑趋势,被子几乎不能将它盖得严实。和它身体的其它部位相比,他的许多腿显得可怜的单薄、细小,这些细小的腿在他跟前,在他眼皮下无依无靠地发出闪烁的微光。
他现在站得相当的直,穿着平整的、带金链扣的蓝色制服,像商业学校的侍者穿的衣服一样。衣服的领子高而且硬,上面露出一个有力的夹下巴。浓密的眉毛下一双黑色的眼睛射出神采奕奕的光辉,他的零乱的白发向下梳理,梳得十分精细而且光亮生辉。
清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烦躁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蟑螂……
她原来是个最美的姑娘,许多人都希望要娶她。她周身无处不美,而最美的是她的头发。这是有一个见过她的人告诉我的。据说有一次在女战神庙里,海神涅普图努斯把她奸污了。女战神连忙回过头去,用盾牌遮住了自己的眼睛。为了给这姑娘以应得的惩罚,女神就把她的头发变成了一堆丑恶的蛇。
不,我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出路,左边或右边,随便哪个方向都行。我别无他求,哪怕这出路只是假想出来自我安慰,我的要求极低,所以不会再有更大的失望。向前,向前!只要不是只抬着胳膊贴在一块木箱板上一动不动 今天我很清楚地明白了,没有内心极大的平静我永远都別想出去。我能有今天确实要归功于我在船上时头几天的镇静,而我镇静的功劳应当属于船上的人们。
我们心情舒畅,唱着歌挤成一团。一个人把自己的声音混入别人的歌声中,他就仿佛被一个鱼钩钩住了。
世界对穷人所要求的一切都最大限度地落到了他们的身上。
长年累月的观察甚至使他跟守门人皮衣领子上的跳蚤也混熟了,他也求那些跳蚤帮他去说服守门人。
格奥尔格搜寻父亲的目光。——“在商行里,他可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他想,“瞧他现在叉开腿坐在这里,双臂交叉在胸前。”
“啊,格奥尔格!”父亲边说边立刻向他走过去。走动时他的厚睡衣敞开,下摆在他的四周飘动——“我的父亲还一直是个魁梧的人,”格奥尔格心中暗想。
我在自己的家里,在那些最好、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陌生人还要陌生。
没有人能指明它们的方向,很多人手握长剑,可是只能挥舞着它们,而想要追踪者它们的眼光透着迷惘。 正因如此,也许像布塞法路斯那样埋头于法律书籍才是最好的。他是自由的,两肋可以不受骑马者的大腿压制,在宁静的灯光下,远离亚历山大战役的喧嚣,阅读着,翻动着我们古老卷册的书页。
那我必须自己来帮助自己(苦诉有什么用处),只是我不可以稍显匆忙地离开这里
幸福并不取决于财产。幸福只是定向问题。这就是说,幸福者看不见现实的黑暗边缘。
人们为了获得生活,就得抛弃生活。
其实那只不过是一条普通的脖套。就像人们常常把超然存在当成逃遁一样。
不可能存在没有真实的人生,真实恐怕就是指人生本身吧。
你对这些话的领会程度,取决于你的孤独有多深。
光勤劳是不够的,蚂蚁也非常勤劳。你在勤劳些什么呢?有两种过错是基本的,其他一切过错都由此而生:急躁和懒惰。
向后倒下时,我像得到解救似的感到,它无可挽回地淹死在我那填平所有洼地漫过一切堤岸的血泊里。
青年充满阳光和爱。青年是幸福的,因为他们能看到美。这种能力一旦失去,毫无慰藉的老年就开始了,衰落和不幸就开始了。谁能保持发现美的能力,谁就不会变老。。
在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柄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共同的是:一切。
我们清醒地穿过梦境:我们自己只不过是过去的岁月的一个幽灵。
艺术向来都是要投入整个身心的事情,因此,艺术归根结底都是悲剧性的。
我们为什么要为原罪而抱怨?不是由于它的缘故我们被逐出了天堂,而是由于我们没有吃到生命之树的果子所致。
是的,人太可怜了。因为他在不断增加的群众中一分钟一分钟地越来越孤独。
害怕失去饭碗,这种恐惧心理败坏了人的性格。生活就是这样。
生活中有种种可能性,而在一切可能性中反映出来的只是自身存在的一种无法逃脱的不可能性。
我又不怕死,一命换一命。
待在原地不要动,大千世界会主动向你走来。
富人的奢侈生活以穷人的贫困为代价。
对于健康的人来说,生就是对人必有一死这种意识的无意识的、没有明言的逃遁。疾病总是警告,同时又是较量,因此,疾并痛苦、病痛也是虔诚的极重要的源泉。
我永远得不到足够的热量,所以我燃烧——因为冷而烧成灰烬。
人们憎恨旧的牢房,请求转入一个新的牢房。在那里人们将开始学会憎恨这新的牢房。
我们就像被遗弃的孩子,迷失在森林里。当你站在我面前,看着我时,你知道我心里的悲伤吗,你知道你自己心里的悲伤吗?
目的虽有,却无路可循,我们称之为路的无非是踌躇。
从某一点开始便不复存在退路。这一点是能够达到的。
字必须加以精确的界定,否则,我们会跌进完全意想不到的谷底。我们爬不上削得光滑的石阶,反而会陷在烂泥之中。
精神只有在不成为支撑物时,它才会自由。
如果没有这些可怕的不眠之夜,我根本不会写作。而在夜里,我总是清楚地意识到我单独监禁的处境。
心脏是一座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一间住着痛苦,另一间住着欢乐,人不能笑得太响。否则笑声会吵醒隔壁房间的痛苦。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在与死神的一次遭遇中获胜,会使你强壮起来的。
殉道者们并不低估肉体,他们让肉体在十字架上高升。
人们是永远不可能坦白一切的。甚至往昔那些看上去似乎彻底坦白出来的事情,后来也显示出还有根子留在内心深处。
欲望之泉就是他的寂寞之泉。
从真正的对手那儿有无穷的勇气向你涌来。
真正的道路在一根绳索上,它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的。它与其说是供人行走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
这是对的。每个魔术师都有自己的仪式。比如说,海顿只有戴着扑粉的假发时才作曲。写作也是一种召魔法术。
我爱她,但不能跟她说话,我窥视着她,以便不与她相遇
除非逃到这个世界当中,否则怎么会对这个世界感到高兴呢?
像这只手一样紧紧的握着石头。可是他紧紧握着石头,仅仅是为了把它扔得更远。
艺术是一面镜子,它和钟表一样,有时也会‘走快’。
人无法通观自己,他处在黑暗中。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梦揭开了现实,而想象隐藏在现实后面。这是生活的可怕的东西——艺术的震撼人的东西。
有信仰的人无法给信仰下定义,没有信仰的人下的定义则笼罩着杯嫌弃的影子。
人只因承担责任才是自由的。这是生活的真谛。
一不抱怨,二不解释,绝对是个人才。
他也深信,他之所以变声音不是因为别的而仅仅是重感冒的朕兆,这是旅行推销员的职业病。
你可以逃避这世上的痛苦,这是你的自由,也与你的天性相符。但或许,准确地说,你唯一能逃避的,只是这逃避本身。
有些人通过指出太阳的存在来拒绝苦恼,而他则通过指出苦恼的存在来拒绝太阳。
所有人类的错误无非是无耐心,是过于匆忙地将按部就班的程序打乱,是用似是而非的桩子把似是而非的事物圈起来。
物质必须用精神进行加工。这是什么?这就是体验,不外乎体验和把握体验的东西。
要生活得漂亮,需要付出极大忍耐,一不抱怨,二不解释,才是个人才。
我要好好的活着, 用心的活着, 等到有一天 上天把他欠我的全都还给我!
当格里高.萨姆莎从烦躁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发现他在床上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跳蚤。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