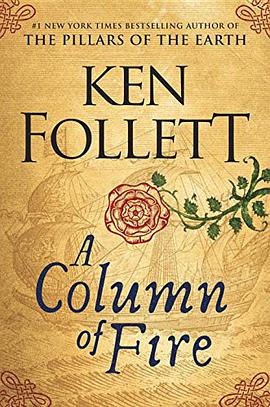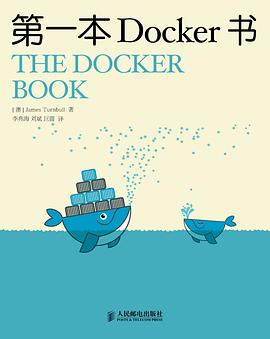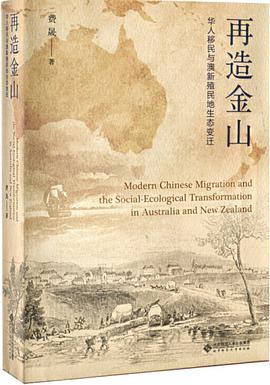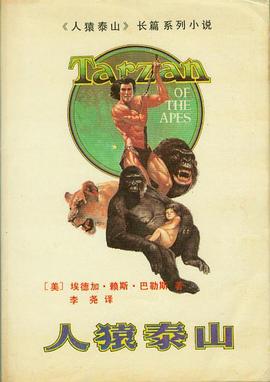内容简介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融会了他数十年人生经历与治学体会,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观察现代中国之来路,给人启发良多。英文原本推出后,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并两次获得美国书卷奖历史类好书的提名。
......(更多)
作者简介
黄仁宇 (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其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
......(更多)
目录
自序
第一章 万历皇帝
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第六章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第七章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参考书目
附录一
附录二
《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更多)
读书文摘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的发展,必然受到限制。即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 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宗,他们都是大音乐家、画家、诗人和词人,只因为他们沉湎在艺术之中,以致朝政不 修,有的还身受亡国的惨祸。
难道一个人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了在御前为皇帝作顾问的条件?难道学术上造诣深厚,就能成为大**家?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自古以来的圣君明主以德行治理天 下,艺术的.精湛,对苍生并无补益。像汉成帝、梁元帝、陈后主、隋炀帝和宋徽宗、宁
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
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 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难道一个人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了在御前为皇帝作顾问的条件?难道学术上造诣深厚,就能成为政治家?二十五年前,翰林院修撰徐时行(当时他尚未姓申,仍袭用外祖徐姓)也曾对这些问题发生疑惑。但是今天的大学士申时行对此早已涣然冰释,理解了其中的精微奥妙,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这一帝国既无崇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
传统的**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据此而作进一步探索,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恻动人,情节也真实可信。
人的进学中举,表面上似乎只是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的结果,实则父祖的节衣缩食,寡母 的自我牺牲,贤委的茹苦含辛,经常是这些成功的背景。无数的条文和墓碑,可为例证。 这些文章多有出自儿子或丈夫的手笔,其中歌颂母亲或妻子给他们的赞助扶持,文句悱
万历的看法是,邹元标和其他诤谏者并非对他尽忠,而是出于自私自利,即所谓“讪君卖直”。这些人把正直当做商品,甚至不惜用诽谤讪议人君的方法做本钱,然后招摇贩卖他正直的声望[lizhigushi.com]。
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箓。
在抗倭**中功绩最为卓着的戚继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的天才的将领。他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
因为所谓“自己”,不过是一种观念,不能作为一种物质,可以囤积保存。生命的意义,也无非是用来表示对他人的关心。只有做到这一点,它才有永久的价值。这种理想与印度的婆罗门教和佛教的教义相近。印度的思想家认为“自己”是一种幻影,真正存在于人世间的,只有无数的因果循环。儒家的学说指出,一个人必须不断地和外界接触,离开了这接触,这个人就等于一张白纸。在接触中间,他可能表现自私,也可能去绝自私而克臻于仁。
帝国的官僚**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成千成万的官僚,在维护成宪的名义下保持各方面的平衡,掩盖自己不可告人的私利。
科举制度的重要性又在社会风气中得到反外一个读书人如果不入仕途,则极少有机 会表现他的特长,发挥他的创造能力;也极少有机会带给一家、一族以荣誉。所以一个
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漫修远,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约,积铢累寸,首先巩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抵押权,由此而逐步上升为地主。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在多数情形之下也为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是一个人或至多几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
他们也要阐明三代以来的王道至今依然适用,即一个良好的政府务必选贤任能,同时在社会上提倡诚信与和谐。总而言之,道德至高无上,
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
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
这种经验,使他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大凡高度的概括,总带有想象的成分。
但是迷信与非迷信,其间的分野也可能极为模糊。例如,当一个人强迫自己对一件事情、一种前途建立信念,则其与宗教式的皈依就相去极微。因为凡是一个人处于困境,他就不愿放弃任何足以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即使这种可能性极为渺茫,没有根据,他也要把它作为自己精神上的寄托。
我们的军官在长期训练中所培养的严格和精确,退伍以后竟毫无用武之地。他会发现在军队以外,人们所重视的是安详的仪表、华丽的文辞、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圆通无碍的机智。——总而言之,和他已经取得的能力恰恰相反。
另一类人物则干脆是为了争权夺利,他们利用道德上的辞藻作为装饰,声称只有他们才能具有如此的眼光及力量来暴露张冯集团的本质。而张冯被劾之后在朝廷上空出来的大批职务,他们就当仁不让,安排亲友。
在抗倭战争中功绩最为卓着的戚继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的天才的将领。他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
如果将领当机立断,指挥部队迅速投入战斗,那是贪功轻进,好勇嗜杀;要是他们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有利的战机,那又是畏葸不前,玩敌养寇。
但是他与洪武皇帝都没有想到,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镇子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
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这样的人不会相信为人处世该有阴阳的分别,他肯定会用他自己古怪的标准要求部下和上司。对他应该怎么分派呢?看来比较稳妥的办法是让他升官而不让他负实际的责任。
社会物质文明(即李贽所谓“文”)往前发展,而国家的法律和组织机构不能随之而改进,势必发生动乱。
在王朝制度下,很难把个人玩忽职守和制度的失败分开。个人应尽最大努力,用自己的才干和自我牺牲来掩盖制度上的弱点。
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
这一帝国既无崇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
据此而作进一步探索,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万历的看法是,邹元标和其他诤谏者并非对他尽忠,而是出于自私自利,即所谓“讪君卖直”。这些人把正直当做商品,甚至不惜用诽谤讪议人君的方法做本钱,然后招摇贩卖他正直的声望。
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箓。
简而言之,帝国的官僚们一意保持传统与稳定,从而丧失了主动性,甚至不惜行事不公。
难道一个人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了在御前为皇帝作顾问的条件?难道学术上造诣深厚,就能成为大政治家?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这一年阳历7月,正当元辅张居正先生去世5周年,皇帝端坐深宫,往事又重新在心头涌现。
因之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
帝国的官僚政治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成千成万的官僚,在维护成宪的名义下保持各方面的平衡,掩盖自己不可告人的私利。
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然而祸来又不即来,等死又不即死,真令人叹尘世苦海之难逃也。可如何!
这些官员之间关系复杂,各有他们的后台老板以及提拔的后进。他们又无一不有千丝万缕的家族与社会关系,因之得罪了一个人,就得罪了一批人;得罪了一批人,也就得罪了全国。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
有时他们身上的自私苟且,还远过于不识字的愚氓。这种不安,或者由此发展而来的内心交战,需要有一种适当的方式来缓解排除。志趣相投的研究讨论,可以触发彼此的灵感,深入探索人生的真谛,俾使内心的不安涣然冰释。
他降谕工部,要工部如实查报,张居正在京内的住宅没收归官以后作何区处:是卖掉了,还是租给别人了?如果租给别人,又是租给谁了?
其实,长期的道德沦亡,即已标志社会形态和其组织制度的脱节。
在他执政的时代,在名义上说,文官还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则已包罗了本朝的出色人物,成为权力的源泉,也是这一大帝国的实际主人。
例如经过皇帝批准,人事有所任免,文渊阁公布其原因,总是用道德的名义去掩饰实际的利害。因为本朝法令缺乏对具体问题评断是非的准则,即令有时对争执加以裁处,也只能引用经典中抽象道德的名目作为依据。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这里的地下玄宫,加上潮湿霉烂的丝织品和胶结的油灯所给人的感觉,却是无法冲破的凝固和窒息。他朱翊钧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后被称为神宗显皇帝,而几百年之后他带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是命运的残酷。
开国时的理想和所提倡的风气与今天的实际距离已经愈来愈远了。很多问题,按理说应该运用组织上的原则予以解决,但事实上无法办到,只能代之以局部的人事调整。
身为一个天津人,你没有为上海的建设作出任何贡献,你不配做北京的好儿女,我代表广州人民鄙视你。
所以说来说去,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此亦即鼓舞士气,发挥精神上的力量。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