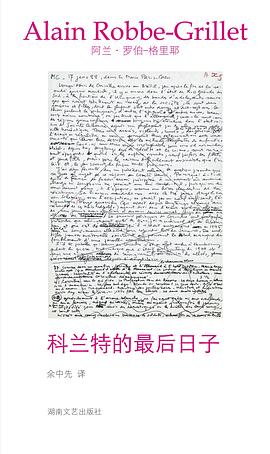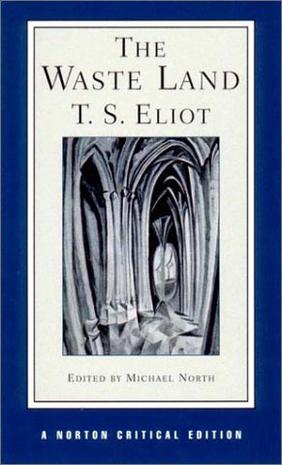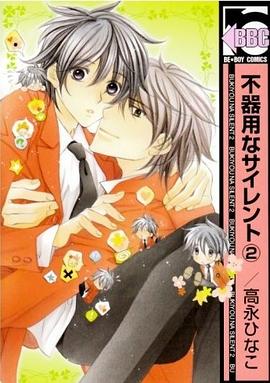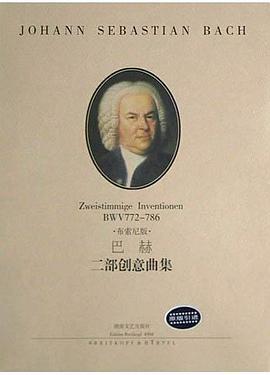内容简介
《科兰特的最后日子》是构成阿兰·罗伯-格里耶奇特自传的“传奇故事”三部曲的完结篇。显然在此 “我” 不可能全然理性而稳固地符合他自己。从政治错误和反常情欲开始,主题无疑在游荡中这样自我构建起来,通过已成废墟的过去和贞洁的未来。这个精神分裂的我于是将在那些活着的可证实的瞬间和那些让人内心感到如同现实的真实片段的虚构里化成肉身。
于是亨利·德·科兰特这个人物,越来越不具历史性,越来越迷幻,从此可以放任关于他的存在问题的驳斥。而身份的浮动非常“自然”地实现了:科兰特,煽动者和南半球巴西边境的非法交易(交易什么?)者,罗伯-格里耶,在纽约的教授,他或他,在布列塔尼岬角上一座废弃的城堡里被吸血鬼未婚妻咬伤而濒临死亡。
......(更多)
作者简介
......(更多)
目录
写作、古老海洋、抚摩的运动。对和谐的关注。乌拉圭海滩以及浴场女子、海浪、岩礁、鸬鹚在“猫咪”,大海以它带锯状肌肉的女阴把我捕捉法兰西堡港湾的海上遭难。慈悲悯人的逆戟鲸海岛上的我的小未婚妻。展放在橱窗中的十二个准备殉道的初领圣体的少女模特少年卡特琳娜在里昂火车站,作为穷大学生的我自己重新当教授。刻苦的研究。在警戒和淹溺之间的一种被穿透的自传圣路易斯的仙人掌。秋季的风。一场飓风扫荡了麦尼尔。我的小姑娘身处于灾难之中。躲过了灾难的昂热丽克麦尼尔的清理工作。巴士拉的椰枣林。科兰特游荡在附近科兰特在马克西米连咖啡馆的平台上,看着如花似玉的姑娘们在假装着玩球。一头浓密白发的德国人的出现。玛丽-昂热(?)和她所谓的父亲跛脚的黑人老妇,售卖惹人麻烦的明信片的女小贩。被拍摄下来的科兰特和他的重影。对一个同谋者网络的怀疑入选美人的虚假亲人成了潜水的鸬鹚。趣味和价钱。尽管他不信任一个过于知情的卖主,爱好鲜柔人肉的买主还是同意,在他吕泰西亚旅馆套间中接待他和玛丽一昂热。装饰着蓝色闪光片的纤细舞鞋,新鲜的血迹塔蒂娅娜·格罗斯曼在巴黎的吕泰西亚旅馆,在巴比伦(长岛),在马里安巴德。和劳申伯格一起在石头上印刷。吕泰西亚书店,钱拉·马克莱和他奇特的商业经营方法。对书籍的考虑。批评家圈子和我的评委生涯从马提尼克归来。圣日耳曼林荫大道的午夜出版社。朗布里奇和我的《弑君者》。我自己在他的梦幻者角色中。热罗姆·兰东和痛苦中的作品手稿。我的侦探式写作新计划。乔治的朋友们。昙花一现的机密杂志擅入自己房子里的兰东。整整一帮人的敌意。面对资本世界的小小才华。孤独与统治。信任感:一个犹太故事一个新的兰东:青春的欢快、博爱、对文学的酷爱。《橡皮》的手稿在午夜出版社。一张蓝色的封皮。如同在一座磨坊中科兰特和德国人在吕泰西亚旅馆。玛丽-昂热展现全裸。奥古斯特·马纳莱画的《奴隶贩子》。沾有血迹的蓝色鞋子。在麦尼尔的昂热丽克的姿势。抚摩,少女的敏感和买主的保留。被撕下了面具的科兰特保持警惕的科兰特。封·德·里夫教授,心理学专家。两个身穿白色服装的年轻男人在南洋杉下。女俘虏的最佳年龄。金发还是棕红发。麝香味,耳光和爱的亲吻科兰特在布列塔尼古老炮台中跟他零乱的手稿在一起。金三角的甜美而又残酷的回忆。海浪的拍打,朴素的家具,沉重的(几乎是魔幻的)椭圆形镜子和女妖魔似的硕大橱柜。烟火色的壁炉、炮眼、煤油灯色情的讨价还价。科兰特被引诱进了陷阱中。公证婚礼的好处。失踪和严重的罪行。玛丽-昂热作为喜欢(严厉的)老头子的典型小姑娘。南洋杉下的两辆黑色摩托车反野少年的战争,他们的残暴,他们的毁灭。歌剧院和它的寄宿者们。被选中的女孩子的审讯和最后刑法。针对科兰特的无根据的指责究竟在哪个日子,为了什么理由,他离开了法国。昂热利卡·冯·萨罗蒙。秘密使命。作为政治一工业的俱乐部的金三角。“共同政体”,它的乌托邦,它的信徒“共同政体”在《橡皮》中的体现。该书在法兰西俱乐部和处境不稳定的午夜出版社出版。和热罗姆一起在莱茵河旅行。他和朗布里奇分手。布雷内的插曲。旧妓院中窥淫者的小房间我在午夜出版社的小办公室。阅读手稿。和热罗姆的长时间讨论。我在加桑迪街上的顶层住所,它的极端狭小。《窥视者》的写作。花岗岩的海崖和被风暴侵蚀的坡尔斯莫盖古老军事堡垒,在那里,我在我“不可能的心理回想”的废墟中挣扎着,飞向巴拉那河回到马克西米连咖啡馆。我看到我自己的替身安坐在我最喜欢坐的位子上,以我习惯的姿势读着《环球报》。恶心的感觉。在打开的报纸上,有一张照片。第二天,我的位子空了,而我的慌乱有增无减:我不在我自己中,就像《嫉妒》的叙述者那样。第三个亨利·罗宾出现在吕泰西亚旅馆的登记簿上寻找资本。《嫉妒》被加斯东·伽利马拒绝。在午夜社的出版,惨痛的失败。波朗毫无保留地支持我。作为新婚夫妇的卡特琳娜和我当了装修房子的工人。布托的成功和离去。与萨罗特的“作恶者”条约。新小说诞生了新小说家们对集团一说的保留态度。它的历史存在。这些历险者们特有的、绝对的创造性自由。一个异端分子的集团巴西的皇室,1889年我在坎佩尔的洗礼。在海罗伯里斯的吕泰西亚旅馆,我房间里的床对面,堂·佩德罗二世骑在马上的肖像。马的眼睛。镜子中我的眼睛,我脖子下边的两个新鲜伤痕。徒劳的企图,想弄清楚这一星期的日子是按怎样的顺序度过的:错过了与B.的约会,在马克西米连咖啡馆里讨厌的相遇,追踪着我的另一个亨利·罗宾。我的双重影的照片。由黑女人留下的第二张明信片:已经复印在《环球报》上的、一只血迹斑斑的女人鞋受人觊觎的玩粉红皮球的女郎的嘲笑。配发照片的谈色情一性虐待的文章,它那令人不安的细节。屈从,带刺激味的反抗,心醉神迷的惩罚。充满梦想的日本小女子。90年代春天的西贡。《法兰西晚报》上杜拉斯的采访记。《如歌的中板》的初稿。我把书转给午夜社。向真正的出版商致敬,作家们欠他们的债,恩将仇报。我与兰东的团结,我们共同的作品一个我不应该讲的悲愁故事。《巴黎竞赛》画报约我写一篇文章,以祝贺西蒙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我在长岛毕肖普的家中写这篇文章:《风》的手稿,我与作家的会见,它的附加部分,它的朴实克洛德荒唐的愤怒。热罗姆的生气。两年后短暂的会面伟大的才子们个性中的渺小。我的同类对我的提防。我万分幸运地认识了兰东。《巴黎街道词典》和我们的“词典”,在主流批评中被接受之概念的词典。过多的会议,混乱的讨论,破坏午夜出版社,自由的空间。为什么不是相互影响的空间呢?理论,就是永远地打问号。相互的承认克洛德·西蒙和亨利·德·科兰特在佛兰德危险的公路上。受伤的腿。浑身上下虚弱无力。南洋杉的影子,和B.的约会,依次不正常的睡眠。两个穿白衣服的补充部队士兵和他们的摩托车。最靠近的那个人拿住了黑女人兜售的照片,并抬头朝向科兰特的窗户。一期《侦探》塞到了他的门下读着有关神秘谋杀案的配有照片的文章,我试图回忆起谁是这个指控者西蒙(让-科尔,或皮埃尔)。这个人的证词。第一个亨利·罗宾之死。为警察局而工作的漂亮妓女。一场引出恶果的照相摄影。玛丽一昂热丽卡和鱼叉。穿透了摄影导演脖子的两个洞。血迹斑斑的蓝色女鞋的形象回返。模模糊糊的死者照片科兰特走下庞大的楼梯。“亨利先生。”第三个亨利·罗宾去听电话。第二个跑腿的侍者,接着又是另一个。科兰特上了一辆高级轿车,在后视镜中发现了那两个摩托手,取消了在鲁道夫咖啡馆与B.的约会。开车者嘲讽式的撇嘴。想到玛丽-昂热穿着极其紧身的游泳装,走在大道上,她的舞鞋提在手上,啃着一个青绿色的苹果,经过克里斯蒂安-查理咖啡馆的门口。在被挪动过的后视镜中,司机瞥来过分注意的一眼,科兰特下意识地把手伸向自己的脖子在咖啡馆前宽阔的港湾和大道边上的椰枣树之间,玛丽一昂热在突如其来的风暴中跳舞。一个白发男子在窗玻璃后面。在她玩着皮球的海滩上,一个画家试图抓住情景,他举起的画笔如同乐队指挥手中的指挥棒。充满着吞噬小姑娘的钝吻鳄的佛罗里达沼泽地。和一个暖昧的舵手一起在海湾的小岛之间航行。停靠在一片刺棱着黑色牙齿的淤泥上。遗弃给了海蟹们的精致的女鞋在活岛的窝巢之问,死去的鹈鹕悬挂在黑乎乎的红树的树枝上。一片恶臭。我那肌肉发达的女同伴回收被铁条包封着的小箱子。荒凉的码头,或者说,我们把船停靠在被遗弃的货场附近。七个满身血淋淋的宰鱼人呆在了那里,小刀子停留在一条马尔林鱼上的半空中。卸下沉重的小箱子波普绘画艺术的叙述结构。陪伴着克洛德·西蒙穿越索霍的艺术画廊。废墟的美国。一个犹太人小肉铺的陈迹。昆廷·里策尔的一个画展。使人发愣的画:读《环球报》的人从他那摊开的报纸后面监视着来访者鲍厄里街道上的一群围观者。当地臭味相投的一帮人。从天而降的金发天使浸在一大摊鲜血中。她那带黑色‘花边的连衣裙翻卷着,她的姿势优雅无比。警察们雷鸣般喧闹地匆匆赶到。身穿晚礼服的世俗集团,死去的年轻女子可能属于这个团体。全体静止,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又一次在萨尔索玛焦雷温泉疗养地。亚述一巴比伦建.筑的过分之处。贞洁的废墟的寂静。一个停下来的女精灵的显现。她的重影以谜一般的手势指向古斯塔夫·莫罗的巨幅壁画寂静之声。浮士德、斯巴达的海伦和永生不死。伊瑞娅和青春之源泉。三道门:永恒或者虚无。我的来历被揭示。2450岁。我那无信义的阿里阿德涅的雕像胳膊动了一下第一道门轻柔地把我吸了进去。白色大理石的巨大的阶梯剧场。身穿托加的不多的几个观众以及他们的影子。最下面,在剧场中心,一些雕塑家在十几个面带欣喜微笑的年轻姑娘身上镌刻金色的花纹图案。又回到走廊中。第二道门,我使劲地推都推不开。蓝眼睛的年轻女护士以及她的一群影子般的复制人一排排地坐在诊疗椅上,对面站立着一个展览模型似的阿波罗,他的性器官英姿焕发地勃起着什么法庭?伊瑞娅为我打开了第三道门。在迷迷蒙蒙的浓雾中,一群老人分散地坐在同样的漆成白色的椅子上,观望着空无。一部看不见的无声电影。 《去年》,我自己的嗓子发出的声音古老欧洲与光明帝国的废墟。一个晚成的小说家的突然回顾。我那在岁月的风暴中昙花一现的城邦。面对一群脱缰野马般的精灵,科兰特固执地抵抗着。我在哪里?最后的故事。心灵如同不稳定的颗粒在翻滚。一种新的生命能量不断在我的身外投射出我来。现代(后现代?)小说如同一个活动的空间和瞬间中的物质因素,同固执的清晰相对立科兰特骑马穿越一个被炮火摧毁了的小城镇烧焦的废墟,遍地新积的白雪。一幅黑自绘画。新希腊风格建筑物的片断。一匹煤玉般乌亮的马低头伸向一具敌军中尉的尸体。他身穿一套同亨利伯爵穿的那套军装(索米尔军校的制服)十分相像的黑色军装。纳粹小说家库尔特·科兰特。死去的德国军官的姓名以及他令人心烦的身份照片。在一瞬问中,玛丽-昂热被撞见正在穿衣服,那是在做完爱之后,要不,就是一次处决的淫秽画面?由马克·坦西建造起来的相同本体与相同外表的墓地《弗兰德公路》《情人》和《照相机》《意义的逻辑》。所谓的库尔特·冯·科兰特,如“亨利·罗宾”本人那样,并没有带假的军方证件,以掩饰自己玛丽一昂热的身份?一张由科兰特拍的照片。在不可触摸的尸衣下的男女同体者。卡隆的“黑水仙”和《水仙号上的黑家伙》。我的负面重影给了我一记死神之吻在冬天一片雪白的公园里的一头大野猪。又是一个被毁坏的栅栏。复活节的那个星期,雪的风暴和魔幻的钟声。我们的朋友被弄得迷迷糊糊。是警钟,还是由拉克鲁瓦一儒冈作的诅咒弥撒?麦尼尔的简陋教堂巴尔贝的亲戚科兰特听到,在他的要塞堡垒下传来海浪打在岩石上的低沉的轰击声。通过勘探地下的洞穴,他发现有一条通道,通向一些在最后一次大战中使用过(用作什么呢?)的较新的大厅。在水泥板墙上留下的谜一般的符号。可能是一个监狱?自然的洞穴和通往大海的出口悬崖脚下五花八门的幻象:风云之团停息在岩石群中。三匹公马纹丝不动地注视着我。它们是怎样来那里的呢?在布列塔尼海岛上的圣科兰廷之马科兰特在吕泰西亚旅馆中醒来。两个补充部队的摩托手始终在南洋杉底下坚守岗位。床单上沾上了新鲜的血液。一个被吸血鬼啮咬的叙述者。三个拍照片的侦探的擅入。他们精确无比而又默默无闻的工作昆廷·里策尔在索霍画廊中展出的一幅引起人们惊慌的十分逼真的画。艺术批评家受到刺激。警车在伊斯特河附近,一个宁静而又可疑的街区。平庸的大都市背景粘涂在了生存之中。一个男子凝滞在他的窗户后。自然灾难的白色灰烬。三个迟钝的人物呆在十字路口。这些令人不安的侵略者中的其他六个人停在了行走当中。他们的孤独我自己的形象,跟他们的一模一样,出现在一家被遗弃的店铺的窗玻璃中。我同众人同样的臃肿、笨重,我从中汲取到一种新的力量。忍受苦难的其他同志。在一条长凳上反方向的奇遇。团结经过多次在东南亚和欧洲的旅游,重新回到纽约。电影的计划。麦尼尔的修复工程。废墟的世界。从乔治·西格尔的作品,到萨特的作品。后者的智力活动萨特与新小说。121人宣言。《马里安巴德》,遭诅咒的电影,在威尼斯电影节上突然改变了地位。《现代》杂志上的文章。萨特的难堪。勇气、慷慨以及缺乏个性《马里安巴德》与介入态度。在列宁格勒友好的重逢。斯大林制度的罪过依然存在。艾伦堡和《窥视者》。位于存在主义计划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的新小说。萨特走钢丝对回忆的喋喋不休引起的恶心。被句法所凝固住的瞬间。一道最最细微变化的门槛。结构、行为的量子,以及“clinamen”。梦的叙述。充满谎言的叙述内容杀死了不可能的真实。自传作者毁了他自己的过去“不要回头”:《金三角》《查拉图斯特拉》和卡夫卡式的“桥”。缺少了自我的作家。忧虑和喜悦一张波尔多葡萄酒的标签。围绕着路易十四式城堡的井井有条的葡萄园。光线充沛的餐室。饭桌上一个不合时尚的女子。酒的味道。叙述者看到一瓶疑难重重的“拉维-鲁塞尔城堡酒”后,微笑了年轻的梦幻女子和香水瓶翻转的形象。画有图案的墙纸活动起来。一个潜伏着的猎手。最最柔美的猎物。转瞬即逝的女来访者普拉斯兰岛上厚颜无耻的椰子树。一部梦幻般的电影在远东的流浪:澳门、西贡、下龙湾、吴哥往后呢?和多芒一起在塞舌尔群岛。一次动荡的沿海岸航行。两腿像篮球运动员一样的黑人向导。短短一个钟头的行军。在大雨中上的一堂心理分析课。一种热烈的友谊之情。大地上细微的美。梦见波洛克的作品:头脑中(纠缠成一团)的线条晨露中一张完美无缺的蜘蛛网。而我被囚禁在我的牢房中。手势动作的绘画。各种无谓的企图。我吞噬我自己。胡桃树黑乎乎的枝权这一形象是从哪里来的?科兰特重新走下不断增生着的地下通道。已成废墟的古老部分,以及新近的部分。黏糊糊的、发出磷光的渗出物。罐头鲑鱼,破了的皮球,鸬鹚尸体,水晶球,金褐色的头发,蓝色的鞋子灯火熄灭(已见过)。明亮的四壁。阶梯,汹汹冒犯的海蟹,蓝色的洞穴和神奇的泉眼。月光下椭圆形的水池子。夜间的洗衣女米娜,被诅咒的黄金,变成了一柄火炬的血淋淋的内衣。女巫的询问以及有关的描述。约会科兰特朝着他的庇护所往上走,发现了一枚崭新的芬尼。他的旧伤又复发了。在破碎的镜子中,他看到他那不对称的半死不活的脸。胳膊关节僵硬了。脖子根部两个红红的小洞。手指头上的血。在玻璃球中的吸血鬼米娜。“没有的东西、莱茵河、腰身”。尼伯龙根。诞生地的铁匠炉。红胡子腓特烈。七个牺牲的女俘虏与艺术《环球报》上的照片。福柯和巴西。一家呈碎片坠落的旅馆。巴特和他的庆贺晚会。苏格拉底式的柔情。性爱的错误。游荡和情欲。和福柯一起,以及与巴特一起看脱衣舞。在圣路易斯被抑制的女权主义在特里谢家中见到佩雷克。美第契奖的衰落。五月奖。巴塔耶想讲述死亡:为更好地跃进而后退。选举一个土豆。在穆夏尔换车。很久以来我就已经死了。在苏弗里耶尔火山的一家医院。罗托鲁阿。拉比亚宫的贡朵拉和冰淇淋蛋卷。米尼翁。皮埃尔·昂热丽克。围猎我(无谓地?)等待着米娜。镜子中血淋淋的玛丽-昂热。我署名
......(更多)
读书文摘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