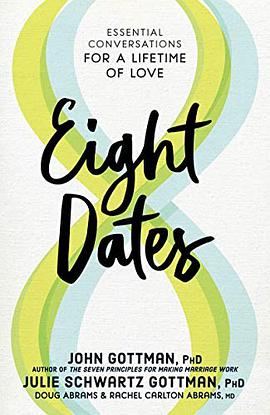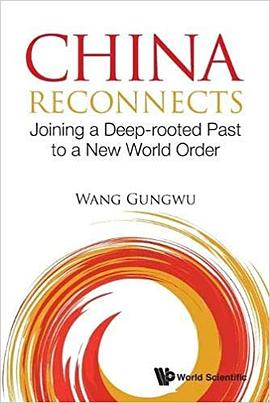内容简介
中译本重印前言
里敦·斯特莱切(Giles Lytton Strachey,一八八○——一九三二)所著《维多利亚女王传》(Queen Victoria)写在六十多年前(出版于一九二一年),现在还没有被人遗忘,我的译本完成于五十年前(一九三五年),现在还辱承新知旧好不时提说,出版社相约重印,亦已有年,如今更殷切催促,我只好忙里偷闲,见缝插针,匆匆校订一遍,聊以塞责,也就不得不作一点说明。
近十年来,英美学术界对于斯特莱切生前所属的布卢姆斯布里(Bloomsbury)文社及其主干维吉妮亚·伍尔孚的研究与资料整理,转趋活跃。去年它的小说家成员摩根·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印度行》被改编成电影上映了,轰动一时。斯特莱切开现代传记文学先河的著作,特别是这部臻于成熟的代表作,必然也会在现代文学史上,以至今后读书人手里,继续放光。近年来国内传记文学表现了兴旺的趋势,文学翻译以及文学翻译研究有了蓬勃的开展。海内外时机的交汇也就使我生平这个第一部专书的试译文,也是我生平仅有的一部传记文学的译本,沾了光,托了福,及时得到了译者自己修订一下,小补艺术良心的机会。
二十世纪只剩最后四分之一了。依我落伍的眼光看来,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期内以至期前后若干年,可能还算是本世纪资本主义世界文学史上的鼎盛时期。当时,十年代、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以至四十年代初,优秀作品,竞放异彩,不少成就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似乎超过了后起的诸多时髦作家更标新立异的作品。
英国十九世纪,主要是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占统治地位的道统,到二十世纪受到了一部分不甘心颓废的“精神贵族”的新挑战,应运而兴起了一种“拆台”(debunking)文学。所谓“拆台”,也无非揭虚表、破迷信、屏滥调,并无造反的意思。文风一变,主要在二十年代,打开了相当繁荣的新局面,也就此呼彼应,成为西方所谓“现代派”一个新阶段的组成部分。
伦敦布卢姆斯布里这个住宅区是这种繁荣的一个典型小中心。那里的伍尔孚和贝尔(Clive Bell)连襟家,每星期四集聚了少数名士,开明,脱俗,不仅有作家、艺术家,还有思想家、经济学家,尽管倾向不尽相同,形成了一个汇合点。早先,老一代小说家亨利·詹姆士偶尔光顾;后来,初享盛誉的诗人艾略特、初出茅庐的小说家衣修午德也间或出入门下。斯特莱切是其中唯一的现代传记文学家。
斯特莱切恰就是以首先好像跟维多利亚时代名人开玩笑起家。他的第一本传记文学集《维多利亚朝名人传》,一九一八年出版,一举成名,使他成为欧洲现代新传记文学的先导。在这前后,他写过一本法国文学史论小书和几本传评小书,一九二八年出版《伊丽莎白和艾瑟克思》,原似乎想写得烂漫一点,终失却平衡,有违他自己写传记的本色。他生平所著数量不多,而以《维多利亚女王传》分量最重,最恰到好处,该是他造极的作品。
他在这本传记里,透过维多利亚女王本人及其左右大人物的王袍朝服,揭示真实面目,公私相衬,亦庄亦谐,谨严而饶有情趣,富于生活气息。
关于这一点,斯特莱切在这本传记里也就表露了他对传记写作的看法。书里写到配王死后,维多利亚女王要臣下为她挚爱的丈夫一再立传,出了几本皇皇巨著,表彰他尽善尽美,问世后并未产生她所预期的效果。“……世人见陈列出来给他们赞叹的人物倒像是道德故事书里的糖英雄,而不像有血有肉的同类,耸一耸肩,一笑,或是轻薄的一哼,掉头而去了。然而在这一点上,世人同维多利亚都有所失。因为实际上亚尔培是远非世人所梦想及的有趣人物。仿佛出于一种离奇的捉弄,一个毫无瑕疵的蜡像硬被维多利亚的恩爱镶嵌进了一般人的想象,而蜡像所表现的人物本身……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第七章第三节末尾)他写这本传记,就作了相反的尝试,根据大量资料,精加汰洗,巧为剪裁,使出了生花妙笔。结果这本书不只是大可参考的历史传记,而更是大可欣赏的传记文学。
我最初注意到这本书,是读了梁遇春(秋心)写的一篇评介长文。斯特莱切死于一九三二年一月,梁在当年六月也病故了,大约只活到前者的一半年龄。这篇遗稿,现在查出,发表在十月一日出版的《新月》第四卷第三期上。编者,显然是还在教我课的老师叶公超,在文后说,这篇文章难能可贵,水平超过了当时英、法、美几种著名文学期刊上发表的纪念专论。梁文里提到的一件小事:总不免带调侃笔调的这本书,刚刚出版,维多利亚的“孙子(乔治五世)看了之后,也深为感动,立刻写信请他到宫里去赴宴,他却回了一封措词婉转的短简,敬谢陛下的恩典,可是不幸得很——他已经买好船票,打算到意大利去旅行,所以还是请陛下原谅吧。”我当时就想,斯特莱切,虽不是酒仙,也有我国古文士“天子呼来不上船”的太白遗风。后来在一九三四年秋后,经也曾教过我课的余上沅介绍给中华文化基金会胡适主持的编译委员会特约译书,我就想起了这本书。所谓“特约”,倒也自由,译者自定选题,只是在我这种受第三级稿酬待遇的年轻人场合,多一道先拿出译文样品送审的手续。成约后我把原注(主要是出处简名)和参考书目全名译出了,为中国读者的便利起见,不仅加了一些注,还编制了“皇室世系图”、“萨克思·科堡世系图”以及维多利亚朝“历任首相表”。译事因旁的工作关系,不能集中进行,拖延到一九三五年三月底,就去日本京都闲住赶译,当年夏天回北平交稿。叶公超原答应为译本写序,我就请他写了直接送编译委员会,我自己去济南教书一学年,也就没有再管交出了的这部译稿。一九三六年底我在青岛译完自选的另一本书(纪德的长篇小说),次年初回北平小住,又交了稿(这部译稿后来完全被丢失了),就离开北平,南下江、浙(当时上海属江苏省)转悠,自由写作与翻译,到夏天在继续为编译委员会译书的时候,“七七事变”发生,接着平津沦陷。不久,我接到在胡适手下为编译委员会办事的一位原北京大学同学的一封信,告以编译委员会结束,没有讲如何处理译稿,却说了一句“树倒猢狲散矣”。写信者可能另有含义,我对“猢狲”二字却非常反感。以后,我在内地各处,后方前方,辗转了二三年,于一九四○年夏天到昆明,不记得哪一位朋友告诉我《维多利亚女王传》译本已在迁到香港的商务印书馆出版,并把他买到的一本送给了我。我见书被印得截头去尾,不见可能是叶公超原没有写交的序文倒也罢了,书后的参考书目全名、世系图、历任首相表等附录,全没有了,非常扫兴。当时我也无心读这本译书。而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把这本译书又出了几版,却从没有找我联系,送我一本。我后来在海内外流寓中,直到“文化大革命”后,几次承友好相赠,丢失了又在旧书店另外买到了送我。现在我手头的一本是一九四七年三月的第三版。
最近我把旧译本匆匆通读一遍,并找到美国初版本(Harcourt,Brace & Co.,一九二一;我记得原先是根据英国好像是Chalto & Windus版翻译的),草草校看一下,发现被错排而不易看出处不少,也有自己的不少疏忽处,现在略加修订。中国语言,三十年代到今,也已有变化,在这里大致都不改了;有些现在看来已并不需要的译注也没有加以删除,音译名也没有照今日通用译名统一修改,只有一些不常见的人地名,都用括弧注出了原文。没有参考书目,从原注出处,无从知道原书全名,不得不重新补译附后。至于原书本没有的“世系图”等,现在也没有工夫补做了,好在这样对于一般读者也并无大碍。
这本书(包括参考书目)在最初试译阶段,我曾请教过一些师友。女王丈夫(Prince Consort),中国过去并没有相当的名称,译成“配王”,好像是叶公超为我的恰切创造。有些地方也曾请教过师辈孙大雨先生以及一些可惜已经记不清的其他师友。数十年来我依然没有学过德文,现在补译参考书目,有几个德文书名重新就近请教了杨一之同志。经过校订,译文欠妥处,想总难免,出版后又得麻烦方家指正。现在也不记得哪位朋友送给我而尚存手头的这本书,纸张陈旧发脆,而我又就在书上作了修订,这会给编辑部和排字间同志带来不少麻烦。凡此种种,我只有在此志谢和预先志谢。
卞之琳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七月二十三日
......(更多)
作者简介
......(更多)
目录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