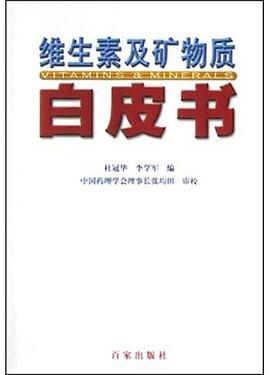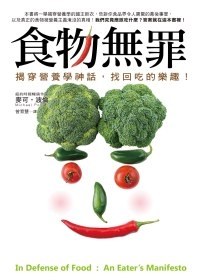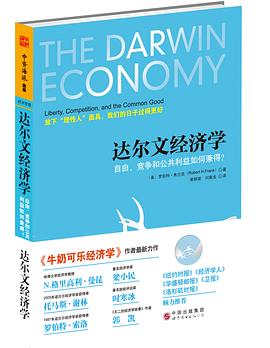内容简介
“刻舟求剑。只是船身的一道又一道愚人刻痕,我们想用它来找掉落时间大河里的某物。”
《求剑》是作家唐诺全新散文作品,23篇关于“年纪、阅读、书写”的重磅思辩。逐渐步入暮年的唐诺把年纪这个视角加进每天的阅读和书写中,变为读和写的新视角、新元素。逐年增长的年纪,迫使书写者时刻面对日益年轻的世界,最大好处是,书籍也跟着年轻起来,由此阅读和书写产生了一种从容跟得上的转动,得以一步步揭露,深入作者希冀抵达之处。唐诺用“年纪”这一独特视角,以其独特的文风和抵达思维尽头的思索,带我们进入伍尔夫、昆德拉、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博尔赫斯、卡尔维诺、赫尔岑、康德、张爱玲、朱天心、阿加莎·克里斯蒂、山田洋次、钟晓阳、侯孝贤、有吉弘行等人的世界,从阅读书写到影视综艺,辨识出那些比文字和影像更稠密更切己的东西,重新打开我们的视野。在创作、书写的世界,有这样一个接近于通则的趋向,一个真的够好,尤其肯于持续盯住世界、盯住人的创作者,随着年纪和他认知的进展、随着时间作用于他身体的种种奇妙熟成,总会缓缓走向真实世界。
编辑推荐
★职业读书人唐诺全新作品,23篇关于“年纪·阅读·书写”的重磅思辨。以“年纪”为视角,重新打开我们的阅读世界。——“我真正期待的仍是年纪”,阅读如刻舟求剑,年纪是船身的一道又一道愚人刻痕,我们用它来找掉落时间大河里的某物。唐诺把年纪这个视角加进他每天的阅读和书写里,变为读和写的新视角、新元素,“整个阅读被重新打开”。“这本书真正把我带进老年,用老年的眼光回头看我熟悉的世界、我熟悉的书、我熟悉的作家所产生的一种角度的转动。”“正因为年纪是稳定前行的,它因此给了阅读和书写一种难以言喻的生动感、一种你从容跟得上的转动,好像每一次都多揭露一点点,更探入一点点。这应该是近年来在我身上所能发生最好的事。”
★“《尽头》之后最好的唐诺。”洗涤、打磨、沉淀、结晶,书籍仍是人类世界最大规模明亮起来的丰饶之地。“我能够想得到的抗癌药物就是书。”——伍尔夫、屠格涅夫、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昆德拉、陀思妥耶夫斯基、赫尔岑、康德、朱天心、张爱玲、阿加莎·克里斯蒂、山田洋次、钟晓阳、侯孝贤、有吉弘行、夏目三久、松子·Deluxe……此次唐诺的笔辐射更广,从阅读书写到影视综艺,带领读者更精细地分辨字里行间与影像背后那些更稠密更切己的东西。“一个真的够好,尤其肯于持续盯住世界、盯住人的书写者、创作者,随年纪随着他认识的进展、随着时间作用于他身体的种种奇妙熟成,总会缓缓走向真实世界。”
★梁文道、杨照推荐。
......(更多)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唐诺,本名谢材俊,一九五八年生于台湾宜兰,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
曾与朱天文、朱天心等创办著名文学杂志《三三集刊》,后任职出版公司数年。近年专事写作,曾获多种文学奖项,朱天文誉之为“一个谦逊的博学者、聆听者和发想者”。《十三邀》第三季嘉宾,许知远称其为“天下第一读书人”。
著有《文字的故事》《阅读的故事》《读者时代》《世间的名字》《尽头》《重读:在咖啡馆遇见14个作家》《眼前:漫游在<左传>的世界》等。
......(更多)
目录
辑一 年纪
1. 一直年轻起来的眼前世界
2. 他们是几岁时写的?
3. 延后二十年变大变老
4. 身体部位一处一处浮现出来
5. 暂时按下不表的死亡
辑二 阅读
1. 携带着的书
2. 结论难免荒唐,所以何妨先盖住它不读
3. 有关鉴赏这麻烦东西,并试以屠格涅夫为例子
4. 黄英哲其书其人,以及少年心志这东西
5. 集体· 递减的生命经历和记忆
6. 一个现场目击者的记忆和说明
7. 再来的张爱玲· 爱与憎
8. 没恶人的寅次郎国
辑三 书写
1. 五百个读者,以及这问题:剩多少个读者你仍愿意写?
2. 第二次庆祝无意义,一本八十几岁的小说
3. 将愈来愈纯粹
4. 重写的小说
5. 请稍稍早一点开始写,趁这些东西还在
6. 字有大有小· 这是字的本来模样
7. 不愿解释自己的作品,却得能够解释自己的作品
8. 文学书写作为一个职业,以及那种东边拿一点西边拿一点的脱困生活方式
辑四 年纪
“瘟疫”时代的爱情· 在日本
附录
千年大梦
......(更多)
读书文摘
(比方小咖啡馆),我甚至说得出它们何时开的店,也说得出它们大约何时会消失,一个月后、半年后云云,这是比较令人悲伤的部分,这样开店的通常是年轻人,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的钱,虚掷只换来沮丧的生命时间,纯浪费的异想天开梦想,我往往打开始就知道这必死无疑,唯无从劝阻。
因此,较好的方式是一种接近欲擒故纵的诡计,你期待成果,但让它在生活中像仅仅只是一个习惯,或一个工作性的义务,把炽烈的心志设法推远成一个遥遥的光点,像某颗天上的星星那样。
再笨的人都晓得,做某些事(比方讨好所有人)比较容易比较安全,也于己有利,还不花钱,或者就说符合“人性”,但我一直牢记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番话,是他纪念普希金的一次演讲里的:“是的,有这么一些深沉而刚强的灵魂,他们不会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圣物送去受辱,即使是出于无限的怜悯。”
唯恐誓盟惊海岳,且分忧喜为衣粮,惋惜逐渐成为你看人、看万事万物的核心之情,你暗暗多知道了一些,你和世界逐渐发展出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切关系,更准确和更细腻的知心关系(逐渐老去的孔子说法是“知天命”一“耳顺”一“从心所欲不逾矩”);如今,你感觉和这个世界形影不离无话不谈,而且,有些特别的话它好像只跟你一个人讲,包括那个本来遥不可及,但变成你一个人镜子的月亮。
我一生所听到那些被称之为“滥好人”的仿若天使型之人,几乎无一例外该去掉那个“好”字,直接就叫滥人,我以为关键还不在仇怨,而是欲望,道理一样,软弱使他感觉自己一直在容让(也容易衍生为谁都占我便宜,他们都对不起我云云),欲望若只生长却无法满足,很快会膨胀到临界点,便只能以各种阴森森的手段来获取和报复。
原来文学的戏剧性往往只是生命某一处尖端部分的凝视、放大和尝试理解,有时还化学实验般放入到某一个特殊时空状态里来观看它的反应和变化,来确信它,并非外于我们“正常”世界的另一种故事、另一种人。
很多人十八岁以前相信有、相信它成立的东西,不会五十岁以后还成立,生命经历不知不觉教会我们很多事情,逼我们注意到很多事情,也要求我们得忍受很多事情;太多东西在人的世界里都是脆弱乙堪的。所以博尔赫斯才说,很多书、很多故事得趁年轻时候读,到定年纪你就不相信了、读不进去了。
唯恐誓盟惊海岳,且分忧喜为衣粮。惋惜逐渐成为你看人、看万事万物的核心之情。
这不容易啊,人多出点什么,举凡才华,念头,心志、情感、梦想、道德、价值信念,乃至于就只是多出一点善念,更多时候并不是祝福,而是极沉重的负担乃至于危险如怀璧其罪,因为这通常是我们这个世界不要的、排斥的,甚至妒恨的东西,你要养好它,还往往要藏好它。
真正的文学书写及其英勇,博尔赫斯曾这么讲:“我不是一贯正确的,也没有这个习惯。”如此,我们或许就多听懂了这话的其中一层深刻意思了一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目标及其关怀,独特的、延续的、专注的,也是它擅长的,有它源远流长一直在想在处理的东西,不会和现实世界一致,否则文学干吗存在呢?
我们总是较相信电影更好的使用方式是让我们(暂时)摆脱这个纠缠不休的不舒服实然世界,呼应着、承接着以神话以传说以一个个仙侠故事盛装的千年大梦,梦见或更炫目、或更公义、或更满足、总而言之这个现实从不给予我们的一个一个想望世界,或另一种没发生的人生。
有一天,我忽然清清楚楚意识到这个应该早就如此明显的事实一我意识到,我面对着的是一个这么年轻的世界,并且仿佛回春,相对于我,这个世界只能一天比一天、每一样事物不停止地更年轻起来。
如此,你会清清楚楚体认到“成长”,你和你携带着书亦步亦趋,以一种几乎可看得见可丈量、一节一节地明亮起来方式,因为这种前行包含了证实,至少告诉你并不是你一个人的胡思乱想,你确实在“某条已有人走过的路上”,这样很让人安心一也许更明确也更持续的成长感觉不是变大,而是变厚,变得稠密结实,人心的一处一处空隙可感地补起来。
这不急,也感觉不能太急,我如今往往把最想读的那本书稍稍挪后感觉在那之前有不少书最好能先看过,好像是某种热身某种预备,好各自获取较恰当通往它们的路径,以及较正确的心情。
经历不直接就是经验,经历得再加上一个反省思索的过程才是经验,经历的验证。
所以人有时还是说说“大话”吧,好让大东西仍可存在,好让自己保有这样的恢宏视野和感受能力,也好让自己不至于如此琐细不堪、不落入到那种其实不该得意的平庸。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