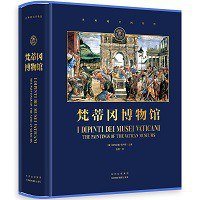内容简介
☆“所有的爱情故事,假如成其为故事,都是从第二次见面开始的。”日本文学史上绕不开的经典,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代表作,侍桁绝版译本,收录《雪国》《伊豆的歌女》两部小说。
☆列车穿过长长的隧道,开往雪国,岛村即将与驹子第二次会面,却意外看见车窗镜面上映现出叶子的美丽面容。三人的愁绪辗转牵连,纷扬的雪花落在每个人的身上, 爱——真的是徒劳的吗?
☆《雪国》并非由一个心碎的爱者所写下的追忆,而是来自一个无能力爱的被爱者的冷眼旁观,某些时刻,他以为这样的爱不过是宛如飞蛾扑火般的徒劳和虚无,但最终,他知晓这爱竟是有幸倾泻在自己身上的壮丽银河。——张定浩 导读
编辑推荐:
▼卡尔维诺曾写道:“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与张定浩重读《雪国》,穿越长长的隧道,抵达爱的银河。
▼选定国内最早的《雪国》译本,1981年侍桁《雪国》单行本。不断被翻译、改编的文学经典,从未被遗忘的爱与忧愁。如果爱注定不能相等,让我们成为爱得更多的那个人。
▼黑白双封×小开本设计,护封“雪国”字体构造出山野、轨道、电线杆、路灯、晒雪场等意象,内封字体设计如同夜间行驶的列车喷薄而出的蒸汽,昼夜交替,简约的具象符号尽显日本文化的幽玄与物哀美学。
......(更多)
作者简介
川端康成(1899-1972),日本作家。1968年以 “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叙事技巧,表现日本人的精神实质”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伊豆的舞女》《雪国》《古都》《千只鹤》《山音》《睡美人》等。
译者侍桁(1908—1987),本名韩侍桁,我国30年代著名作家、评论家、文学翻译家。早年曾留学日本,1930年参加“左联”。30年代曾写作大量的文艺批评文章,辑有《文学评论集》《参差集》《浅见集》。重要译著有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日本川端康成的《雪国》,俄国托尔斯泰的《家庭的幸福》(中篇小说集)等。
......(更多)
目录
读书文摘
她(叶子)的眼睛与灯光重叠的那一瞬间,就像在夕阳的余晖里飞舞的夜光虫
他(岛村)想,驹子大概也像蚕蛹那样,让透明的身躯栖居在这里吧
穿过寂静的几乎连冰水滴落的声音都能听见的杉林,沿着铁路走过滑雪场下方,就有坟地了。在田埂稍高的一角,只立着十来座旧石碑和地藏菩萨。每座坟都显得十分寒碜,光秃秃的,没有鲜花。
玲珑而悬直的鼻梁,虽嫌单薄些,但在下方搭配着的小巧的紧闭的柔唇,却宛如美极了的水蛭环节,光滑而伸缩自如,在默默无言中也有一种动的感觉。如果嘴唇起了皱纹,或者色泽不好,就会显得不洁净。她的嘴唇却不是这样,而是滋润光泽的。两只眼睛,眼梢不翘起也不垂下,简直像有意描直了似的,虽逗人发笑,却恰到好处地镶嵌在两道微微下弯的浓密的短眉毛下。颧骨稍耸的圆脸,轮廓一般,但肤色恰似在白瓷上抹了一层淡淡的胭脂。脖颈底下的肌肉尚未丰满。她虽算不上是个美人,但比谁都要显得洁净。
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
不是欣赏舞蹈家栩栩如生的肉体舞蹈艺术,而是欣赏他自己空想的舞蹈幻影,仿佛憧憬那不曾见过的爱情一样。
玻璃上只映出姑娘一只眼睛,她反而显得更加美了。
但是,这种挚爱之情,不像一件绉纱那样能留下实在的痕迹,纵然穿衣用的绉纱在工艺品中算是寿命最短的,但只要保管得当,五十年或者更早的绉纱,穿在身上照样也不褪色,而人的这种依依之情,却没有绉纱长。
这种孤独驱散了哀愁,蕴含着一种豪放的意志。
待岛村站稳了脚跟,抬头望去,银河好像哗啦一声,向他的心坎上倾泻了下来。
岛村不知怎地,内心深处仿佛感到:凭着指头的感触而记住的女人,与眼睛里灯火闪映的女人,她们之间会有什么联系,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大概是还没有从暮景的镜中清醒过来的缘故吧。他无端地喃喃自语:那些暮景的流逝,难道就是时光流逝的象征吗?
岛村看见这种悲愁,没有觉得心酸,就像是在梦中看见了幻影一样。
叶子的声音美得不胜悲凉,美到消散了温度。纯粹的声音从纷扰琐碎的时光中穿越而来,从生到死,从昂然走向衰亡,镜中的影像,结霜的车窗。
这笑声清越的近乎悲戚。
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
缀满银河的星辰,耀光点点,清晰可见,连一朵朵光亮的云彩,看起来也像粒粒银砂子,明澈极了。
茫茫的银河悬在眼前,仿佛要以它那赤裸裸的身体拥抱夜色苍茫的大地,真是美的令人惊叹不已。
溪中多石,流水的潺潺声,给人以甜美圆润的感觉。
驹子撞击墙壁的空虚回声,岛村听起来有如雪花飘落在自己心田里。
人的感情连最易损的绉绸都不如。因为那些绸缎至少可保存年,而人的依恋之情远比此短。
白花花的一片银色,好像倾泻在山上的秋阳一般。
有朝一日,对生命也心不在焉了。
灯光从她的脸上闪烁而过,却没能将她的面孔照亮。那是远远的一点寒光,在她小小的眸子周围若明若暗的闪亮。当姑娘的星眸同灯火重合叠印的一刹那顷,她的眼珠儿便像美丽撩人的萤火虫,飞舞在向晚的波浪之间。
她的眼睛同灯光重叠的那一瞬间,就像在夕阳的余晖里飞舞的妖艳而美丽的夜光虫。
这种虚伪的麻木不仁是危险的,是一种寡廉鲜耻的表现。
叶子近乎悲戚的优美的声音,仿佛是某座雪山的回音,至今仍然在岛村的耳边萦绕。
“这样的日子里连音色都不一样啊!”驹子仰头望了望雪后的晴空,只说了这么一句。的确,那是由于天气不同。要是没有剧场的墙壁,没有听众,也没有都市的尘埃,琴声就会透过冬日澄澈的晨空,畅通无阻地响澈远方积雪的群山。虽然她自己并不自觉,但她总是以大自然的峡谷作为自己的听众,孤独地练习弹奏。久而久之,她的弹拨自然就有力量。这种孤独驱散了哀愁,蕴含着一种豪放的意志。
这是一种错觉。因为从姑娘面影后面不停地掠过的暮景,仿佛是从她脸的前面流过。定睛细看,却又扑朔迷离。车厢里也不太明亮。窗玻璃上的映像不像真的镜子那样清晰了。反光没有了。这使岛村看入了神,他渐渐地忘却了镜子的存在,只觉得姑娘好像漂浮在流逝的暮景之中。这当儿,姑娘的脸上闪现着灯光。镜中映像的清晰度并没有减弱窗外的灯火。灯火也没有把映像抹去。灯火就这样从她的脸上闪过,但并没有把她的脸照亮。这是一束从远方投来的寒光,模模糊糊地照亮了她眼睛的周围。她的眼睛同灯火重叠的那一瞬间,就像在夕阳的余晖里飞舞的妖艳而美丽的。
在做扑朔迷离的记忆中,也只有这只手指所留下的给几许感触,把他带到远方的女人身边。
她那合上的浓密睫毛,看起来好像是半睁着的黑眸子。
岛村正陷在虚无缥缈之中,驹子走了进来,就像带来了热和光。
山野的灯火在她的脸上闪过,灯火同她的眼睛重叠,微微闪亮,美得无法形容,岛村的心也被牵动了。
驹姐说我快要疯了。
月儿皎洁得如同一把放在晶莹冰块上的刀。
这种焦灼不安的样子,像是夜间动物害怕黎明,焦灼地来回转悠似的。
山脚下的河流,仿佛是从杉树顶梢流出来的。
对面的层峦和山麓的屋顶在迷濛的雨中浮现出来。
你连指尖都泛出好看的颜色。
清浅的疏影映在格子窗上,窗外是茂密新绿的竹叶,女子的颈项间仿佛映上一抹杉林的暗绿。黑色的发丝衬托白皙的面颊,隐约感觉到的是空气里来自白雪的凉意。
歌声清澈得近乎悲戚,马上就能引起回声似的。
这是清澈得近乎悲戚的优美的声音,像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一种回响。
她那副样子,好像是在回顾遥远的往昔,才忽然坐到岛村身边的。
抬头望去,银河好像哗啦一声,向他的心坎上倾泻了下来。
雪夜的宁静沁人肺腑。
她好像一个在荒村的水果店里的奇怪的水果,独自被遗弃在煤烟熏黑了的玻璃箱内似的。
由于天气不同,要是没有剧场的墙壁,没有听众,也没有都市的尘埃,琴声就会透过冬日澄澈的晨空,畅通无阻地响彻远方积雪的群山。
岛村感到百无聊赖。发呆地凝望着不停活动的左手手指。因为只有这个手指,才能使他清楚地感到就要去会见的那个女人。奇怪的是,越是急于想把她清楚地回忆起来,印象就越模糊。在这扑朔迷离的记忆中,也只有这手指所留下的几许感触,把他带到远方的女人身边。
她这种情感与其说带有城市败北者的那种傲慢的不满,不如说是一种单纯的徒劳。
但是,看上去她那种对城市事物的憧憬,现在已隐藏在淳朴的绝望之中,变成一种天真的梦想。他强烈地感到:她这种情感与其说带有城市败北者的那种傲慢的不满,不如说是一种单纯的徒劳。她自己没有显露出寂寞的样子,然而在岛村的眼里,却成了难以想象的哀愁。如果一味沉溺在这种思绪里,连岛村自己恐怕也要陷入缥缈的感伤之中,以为生存本身就是一种徒劳。但是,山中的冷空气,把眼前这个女子脸上的红晕侵染得更加艳丽了。
“你来干什么?”“看你来了。”
对城市美好事物的憧憬,隐藏于淳朴的绝望之中,变成一种天真的梦想。
人嘛,都是脆弱的。据说从高处摔下来,就会粉身碎骨。可是,熊什么的,从更高的岩石山上摔下来,也不损毫毛。人如果有一层像熊一样又硬又厚的毛皮,人的官能一定很不一样了。然而,人都是喜欢自己那身娇柔润滑的皮肤。
贫寒之中自有一种强劲的生命力。
岛村仿佛坐上了某种非现实的东西,失去了时间和距离的概念,陷入了迷离恍惚之中,徒然地让它载着自己的身躯奔驰。
在遥远的山巅上空,还淡淡地残留着晚霞的余晖。透过车窗玻璃看见的景物轮廓,退到远方,却没有消逝,但已经黯然失色了。尽管火车继续往前奔驰,在他看来,山野那平凡的姿态越是显得更加平凡了。由于什么东西都不十分惹他注目,他内心反而好像隐隐地存在着一股巨大的感情激流。这自然是由于镜中浮现出姑娘的脸的缘故。
这是清澈得近乎悲戚的优美的声音,像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一种回响。
从嵌在窗框里的灰色天空中,飘进来纷纷扬扬的大雪花。不知为什么,寂静得使人难以置信。岛村睡眠不足,茫茫地望着虚空。
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
杉树亭亭如盖,不把双手撑着背后的岩石,向后仰着身子,是望不见树梢的。而且树干挺拔,暗绿的叶子遮蔽了苍穹,四周显得深沉而静谧。
这是一幅严寒的夜景,仿佛可以听到整个冰封雪冻的地壳深处响起冰裂声。没有月亮。抬头仰望,满天星斗,多得令人难以置信,星辰闪闪竞耀,好像以虚幻的速度慢慢坠落下来。繁星移近眼前,把夜空越推越远,夜色也越来越深沉。县界的山峦已经层次不清,显得更加黑苍苍的,沉重地垂在星空的边际。这是一片清寒、静谧的和谐气氛。
生存本身就是一种徒劳。
镜中的雪越发耀眼,活像燃烧的火焰。
以朋友相待,不向你求欢。
“这样的日子里连音色都不一样啊!”驹子仰头望了望雪后的晴空,只说了这么一句。的确,那是由于天气不同。要是没有剧场的墙壁,没有听众,也没有都市的尘埃,琴声就会透过冬日澄澈的晨空,畅通无阻地响澈远方积雪的群山。
犹如一条大光带的银河,使人觉得好像浸泡着岛村的身体,漂漂浮浮,然后伫立在天涯海角上。这虽是一种冷冽的孤寂,但也给人某种神奇的魅惑之感。
虽然她自己并不自觉,但她总是以大自然的峡谷作为自己的听众,孤独地练习弹奏。久而久之,她的弹拨自然就有力量。这种孤独驱散了哀愁,蕴含着一种豪放的意志。
缀满银河的星辰,耀光点点,清晰可见,连一朵朵光亮的云彩,看起来也像粒粒银砂子,明澈极了。
在遥远的山巅上空,还淡淡地残留着晚霞的余晖。透过车窗玻璃看见的景物轮廓,退到远方,却没有消逝,但已经黯然失色。
黄昏的景物在镜后移动着。也就是说,镜面映现出的虚像与镜后的实物在晃动,好像电影里的叠影一样。出场人物和背景没有任何联系。而且人物是一种透明的幻像,景物则是在夜霭中的朦胧暗流,两者消融在一起,描绘出一个超脱人世的象征世界。特别是当山野里的灯火映照在姑娘的脸上时,那种无法形容的美,使岛村的心都几乎为之颤动。
茫茫的银河悬在眼前,仿佛要以它那赤裸裸的身体拥抱夜色苍茫的大地,真是美的令人惊叹不已。
溪中多石,流水的潺潺声,给人以甜美圆润的感觉。
他坐来的那辆汽车的车辙,清晰地留在雪地上,在星光下,意外的拖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这种焦灼不安的样子,像是夜间动物害怕黎明,焦灼地来回转悠似的。
这是一种错觉。因为从姑娘面影后面不停地掠过的暮景,仿佛是从她脸的前面流过。定睛细看,却又扑朔迷离。车厢里也不太明亮。窗玻璃上的映像不像真的镜子那样清晰了。反光没有了。这使岛村看入了神,他渐渐地忘却了镜子的存在,只觉得姑娘好像漂浮在流逝的暮景之中。这当儿,姑娘的脸上闪现着灯光。镜中映像的清晰度并没有减弱窗外的灯火。灯火也没有把映像抹去。灯火就这样从她的脸上闪过,但并没有把她的脸照亮。这是一束从远方投来的寒光,模模糊糊地照亮了她眼睛的周围。她的眼睛同灯火重叠的那一瞬间,就像在夕阳的余晖里飞舞的妖艳而美丽的。
生存本身就是一种徒劳。
这张脸同早晨雪天映在镜子中的那张脸一样,红扑扑的。在岛村看来,这又是介于梦幻同现实之间的另一种颜色。
披上一层薄雪的杉林,分外鲜明地一株株耸立在雪地上,凌厉地伸向苍穹。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