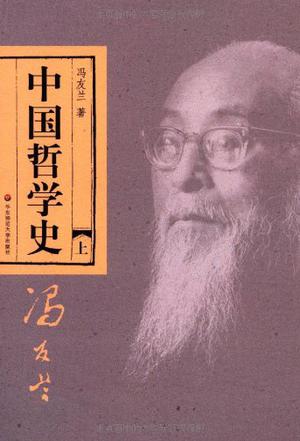内容简介
《黄金时代》是《时代三部曲》之一。 这是以文革时期为背景的系列作品构成的长篇。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年代。那时,知识分子群体无能为力而极“左”政治泛滥横行。作为倍受歧视的知识分子,往往丧失了自我意志和个人尊严。在这组系列作品里面,名叫“王二”的男主人公处于恐怖和荒谬的环境,遭到各种不公正待遇,但他却摆脱了传统文化人的悲愤心态,创造出一种反抗和超越的方式:既然不能证明自己无辜,便倾向于证明自己不无辜。于是他以性爱作为对抗外部世界的最后据点,将性爱表现得既放浪形骸又纯
......(更多)
作者简介
王小波:男,1952年生于北京。他是唯一一位两次荣获世界华语文学界的重要奖项——台湾联合报系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第13届和第16届)的祖国大陆作家。他经历、学历复杂,先后当过知青,民办教师,工人,工科大学生,后到美国兹堡大学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再学计算机,在统计系当助教,回国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
......(更多)
目录
读书文摘
许鞍华:如果观众看这个戏,不了解这么多文人的背景,直接看也可以的。你试想想,他们全都要知道萧红写什么才能看吗?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变成国文课里头的介绍了。他应该是不完整的东西,就是你不知道他是谁,你也能看下去,尤其是外国观众。
那一年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
似水流年是一个人所有的一切,只有这个东西,才真正归你所有。其余的一切,都是片刻的欢娱和不幸,转眼间就已跑到那似水流年里去了。我所认识的人,都不珍视自己的似水流年。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一件东西,所以一个个像丢了魂一样。
于是我想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质,放到合适的地方就大放光彩,我的本质是流氓土匪一类。
但我只是看着他。像野猪一样看他,像发傻一样看他,像公猫看母猫一样看他。把他看到没了脾气,就让我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槌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槌的牛一样。
我坐在小屋里,听着满山树叶哗哗响,终于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我听见浩浩荡荡的空气大潮从我头顶涌过,正是我灵魂里潮兴之时。正如深山里花开,龙竹笋剥剥地爆去笋壳,直翘翘地向上。到潮退时我也安息,但潮兴时要乘兴而舞。正巧这时陈清扬来到草屋门口,她看见我赤条条坐在竹板床上,阳具就如剥了皮的兔子,红通通亮晶晶足有一尺长,直立在那里,登时惊慌失措,叫了起来。
竟敢说自己清白无辜,这本身就是最大的罪孽。照我的看法,每个人的本性都是好吃懒做,好色贪淫,假如你克勤克俭,守身如玉,这就犯了矫饰之罪,比好吃懒做好色贪淫更可恶。
那里的人习惯于把一切不是破鞋的东西说成破鞋,而对真的破鞋放任自流
亚热带旱季的阳光把我晒得浑身赤红,痛痒难当,我的小和尚直翘翘地指向天空http://Www.GuaZe.Com瓜泽网,尺寸空前。这就是我过生日时的情形。我醒来时觉得阳光耀眼,天蓝得吓人,身上落了一层细细的尘土,好像一层爽身粉。我一生经历的无数次勃起都不及那一次雄浑有力,大概是因为在极荒僻的地方,四野无人。
我思故我在,既然我存在,就不能装作不存在。尤论如何,我要对自己负起责任。
我身边带有很多伟大友谊,要送给一切人。因为他们都不要,所以都发泄在陈清扬身上了。
我开始辨认星座。有一句诗说:像筛子筛麦粉,星星的眼泪在洒落。在没有月亮的静夜,星星的眼泪洒在铃子身上,就像荧光粉。我想到,用不着写诗给别人看,如果一个人来享受静夜,我的诗对他毫无用处。别人念了它,只会妨碍他享受自己的静夜诗。如果一个人不会唱,那么全世界的歌对他毫无用处;如果他会唱,那他一定要唱自己的歌。也就是说,诗人这个行当应该取消,每个人都要做自己的诗人。
假如她想借我的身体练开膛,我准让她开;所以我借她身体一用也没什么不可以。
就如世上一切东西,你信它是真,它就真下去;你疑它是假,它就是假的。我的话也半真不假。但是我随时准备兑现我的话,哪怕天崩地裂也不退却。就因为这种状态,别人都不相信我。
陈清扬说,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忍受摧残,一直到死。想明了这一点,一切都能泰然处之。要说明她怎会有这种见识,一切都要回溯到那一回我从医院回来,从她那里经过进了山。我叫她去看我,她一直在犹豫。等到她下定了决心,穿过中午的热风,来到我的草房前面,那一瞬间,她心里有很多美丽的想像。等到她进了那间草房,看见我的小和尚直挺挺,像一件丑恶的刑具。那时她惊叫起来,放弃了一切希望。
她到山里找我时,爬过光秃秃的山冈。风从衣服下面吹进来,吹过她的性敏感带,那时她感到的性欲,就如风一样捉摸不定。它放散开,就如山野上的风。她想到了我们的伟大友谊,想起我从山上急匆匆地走下去
小时候我看到那只公鸡离地起飞时,觉得是个令人感动的场面。它用力扑动翅膀时,地面上尘土飞扬,但是令人感动的地方不在这里。作为一只鸡,它怎么会有了飞上天的主意?我觉得一只鸡只要有了飞上五楼的业绩,就算没有枉活一世。我实在佩服那只鸡。
因为她觉得穿什么和不穿什么无所谓。这是从小培养起来的信心。问题不在于破鞋好不好,而在于她根本不是破鞋。就如一只猫不是一只狗一样。
爱情仿佛结束了,又好像没有到来。我好像中过了头彩,又好像还没有到开彩的日子,这一切好像是结束了,又仿佛刚刚开始。
以前人家说她是破鞋,说我是她的野汉子时,她每天都来找我。那时好像有必要。自从她当众暴露了她是破鞋,我是她的野汉子后,再没人说她是破鞋,更没人在她面前提到王二(除了罗小四)。大家对这种明火执仗的破鞋行径是如此的害怕,以致连说都不敢啦。
首先要当个正直的人,其次要当个快乐的人。
大家都说存在的东西一定不存在,这是因为眼前的一切都是骗局。大家都说不存在的东西一定存在,比如王二,假如他不存在,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的?
我要爱,要生活,把眼前的一世当作一百世一样。
冷雾,雨水,都沁进了她的身体。那时节她很想死去。她不能忍耐,想叫出来,但是看见了我她又不想叫出来。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男人能叫她肯当着他的面叫出来。她和任何人都格格不入。
人活着总要有个主题,使你魂梦系之。
下半截沉在黑暗里,上半截仍浮在阳光中。
我们有伟大友谊,一起逃亡,一起出斗争差,过了二十年又见面,她当然要分开两腿让我趴进来。所以就算是罪孽,她也不知罪在何处。更重要的是,她对着罪恶一无所知。
那时她被架在我的肩上,穿着紧裹住双腿的筒裙,头发低垂下去,直到我的腰际。天上白云匆匆,深山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刚在她屁股上打了两下,打得非常之重,火烧火燎的感觉正在飘散。打过之后我就不管别的事,继续往山上攀登。陈清扬说,那一刻她感到浑身无力,就瘫软下来,挂在我肩上。那一刻她觉得如春藤绕树,小鸟依人。她再也不想理会别的事,而且在那一瞬间把一切都遗忘。在那一瞬间她爱上了我,而且这件事永远不能改变。
既然人饿了就要吃饭,渴了就要喝水,到了一定岁数就想性交,上了会场就要发呆,同属万般无奈;所以吃饭喝水性交和发呆,都属天赋人权的范畴
而X海鹰对我来说就是个痛苦的源泉,我总是盼她掉进土坑。尽管如此,她还是让我魂梦系之。人活在世界上,快乐和痛苦本就分不清。所以我只求它货真价实。
我要爱,要生活,把眼前的一世当作一百世一样。无论如何,我要对自己负起责任。
别人没有义务先弄明白你是否偷汉再决定是否管你叫破鞋。你倒有义务叫别人无法叫你破鞋。
我过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打算在晚上引诱陈清扬,因为陈清扬是我的朋友,而且胸部很丰满,腰很细,屁股浑圆。除此之外,她的脖子端正修长,脸也很漂亮。我想和她性交,而且认为她不应该不同意。假如她想借我的身体练开膛,我准让她开;所以我借她身体一用也没什么不可以。唯一的问题是她是个女人,女人家总有点小气。为此我要启发她,所以我开始阐明什么叫做“义气
放声大哭从一个梦境进入另一个梦境,这是每个人都有的奢望。
一次爱情就像吃了一个巧克力壳的冰棍。开头是巧克力,后来是奶油冰淇淋。最后嘴里剩下一个干木棍。
线条嫣然一笑,展开手中的折扇,扇面上有极好的两个隶字:“有主”。
实际上我什么都不能证明,除了那些不需要证明的东西
人都是为了要表演,失去了自己的存在。
越是无可怀疑的事就越值得怀疑。
我在实验室里踱步,忽然觉得生活很无趣,它好像是西藏的一种酷刑:把人用湿牛皮裹起来,放在阳光下曝晒。等牛皮干硬收缩,就把人箍得乌珠迸出。生活也如是:你一天天老下去,牛皮一天天紧起来。这张牛皮就是生活的规律:上班下班、吃饭排粪,连做爱也是其中的一环,一切按照时间表进行,躺在牛皮里还有一点小小的奢望:出国,提副教授。一旦希望破灭,就撒起癔症。真他妈的扯淡:真他妈的扯淡得很!
寂寞就是可以做一切事的自由。
中的豪杰们,杀人放火的事是家常便饭,可一听说及时雨的大名,立即倒身便拜。我也像那些草莽英雄,什么都不信,唯一不能违背的就是义气。只要你是我的朋友,哪怕你十恶不赦,为天地所不容,我也要站到你身边
每个人活着,都该有自己的故事。
忽然间我感到很烦很累,不像二十一岁的人。我想,这样下去很快就会老了。
“她还说,她无疑是当地斗过的破鞋里最漂亮的一个。斗她的时候,周围好几个队的人都去看,这让她觉得无比自豪。”
幸福,是用来感受生活的,而不是用来比较的。生活,是用来经营的,而不是用来计较的。
指标这种东西,是一切浪漫情调的死敌。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逝,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
这是与生俱来的积习,根深蒂固。放声大哭从一个梦境进入另一个梦境,这是每个人都有的奢望。
所以我保持沉默。沉默就是默认。
所谓虚伪,打个比方来说,不过是脑子里装个开关罢了。无论遇到任何问题,必须做出判断:事关功利或者逻辑,然后把开关拨动。拨到功利一边,咱就喊皇帝万岁万万岁,扳到逻辑一边,咱就从大前提、小前提,得到必死的结论。由于这一重负担,虚伪的人显得迟钝,有时候弄不利索,还要犯大错误。人们可以往复杂的方向进化;在逻辑和功利之间构筑中间理论。通过学习和思想斗争,最后达到这样的境界;可以无比真诚地说出皇帝万万岁和皇帝必死,并且认为,这两点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条光荣的道路一点也不叫我动心。我想的是退化而返璞归真。
其实伟大友谊不真也不假,就如世上一切东西一样,你信它是真,它就真下去。你疑它是假,它就是假的。
在这种夜里,人不能不想到死,想到永恒。死的气氛逼人,就如无穷的黑暗要把人吞噬。我很渺小,无论作了什么,都是同样的渺小。但是只要我还在走动,就超越了死亡。现在我是诗人。虽然没发表过一行诗,但是正因为如此,我更伟大。我就像那些行吟诗人,在马上为自己吟诗,度过那些漫漫的寒夜。
陈清扬说,那一回她躺在冷雨里,忽然觉得每一个毛孔都进了冷雨。她感到悲从中来,不可断绝。忽然间一股巨大的快感劈进来。冷雾,雨水,都沁进了她的身体,那时节她很想死去。她不能忍耐,想叫出来,但是看见了我她又不想叫出来。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男人能叫她肯当着他的面叫出来。她和任何人都格格不入。
于是我想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质,放到合适的地方就大放光彩。
那些小山上长满了草,草下是红土。上午风从山上往平坝里吹,冷得像山上的水,下午风吹回来,带着燥热和尘土。陈清扬来找我时,乘着白色的风。风从衣服下面钻进来,流过全身,好像爱抚和嘴唇。
我坐在小屋里,听着满山树叶哗哗响,终于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我听见浩浩荡荡的空气大潮从我头顶涌过,正是我灵魂里潮兴之时。正如深山里花开,龙竹笋剥剥地爆去笋壳,直翅翅地向上。到潮退时我也安息,但潮兴时要乘兴而舞。
虚伪是伟大的文明。
真实就是无法醒来。
这一点可以说明陈清扬很漂亮,因为她觉得穿什么不穿什么无所谓。这是从小培养起来的自信心。
她和任何人都格格不入。
我想起拉封丹的一个寓言:有两个朋友住在一个城里,其中一个深夜去找另一个。那人连忙爬起来,披上铠甲,右手执剑,左手执钱袋,叫他的朋友进来说:“朋友,你深夜来访,必有重大的原因。如果你欠了债,这儿有钱。如果你遭人侮辱,我立刻去为你报仇。如果你是清夜无聊,这儿有美丽的女奴供你排遣。”
义气就是江湖好汉中那种伟大友谊。《水浒》六十一、当然是你的了。你为科学,拿自己做了贡献,这种精神与自愿献血同等高尚。学校应该给你营养补助,像你这种结了婚,入不敷出的同志能做到这一步,尤为难能可贵。
当我沿着一条路走下去的时候,心里总想着另一条路上的事。
那些日子里北京上空充满了阴霾,像一口冻结了的粘痰,终日不散。
用不着写诗给别人看,如果一个人来享受静夜,我的诗对他毫无用处。别人念了它,只会妨碍他享受自己的静夜诗。如果一个人不会唱,那么全世界的歌对他毫无用处;如果他会唱,那他一定要唱自己的歌。这就是说,诗人这个行当应该取消,每个人都要做自己的诗人。
中年妇女在中国是一种自然灾害,这倒不是因为她们不好看,而是因为她们故意要恶心人!
她简直又累赘,又讨厌,十分可恨。但是后来我很爱她。这说明可恨和可爱原本就分不清。
当时陈清扬也想大哭一场,但是哭不出来,好像被人捏住了喉咙。这就是所谓的真实。真实就是无法醒来。那一瞬间她终于明白了世界上有些什么,下一瞬间她就下定了决心,走上前来,接受摧残,心里快乐异常。
我只愿蓬勃生活在此时此刻,无所谓去哪,无所谓见谁。那些我将要去的地方,都是我从未谋面的故乡。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决定怎么爱,怎么活。
在我看来,存在本身有无穷的魅力,为此值得把虚名浮利全部放弃。我不想去骗别人,受逼迫时又当别论。如此说来,我得不到什么好处。但是,假如我不存在,好处又有什么用?当时我还写道,以后我要真诚地做一切事情,我要像笛卡尔一样思辨,像堂吉诃德一样攻击风车。无论写诗还是做爱,都要以极大的真诚来完成。眼前就是罗德岛,我就在这里跳跃——我这么做什么都不为,这就是存在本身。
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忍受摧残一直到死想明了这一点一切都能泰然处之。
所以就算是罪孽,她也不知罪在何处。更主要的是,她对这罪恶一无所知。
她没法相信她所见到的每件事都是真的。真的事要有理由。当时她脱了衣服,坐在我的身边,看着我的小和尚,只见它的颜色就像烧伤的疤痕。这时我的草房在风里摇晃,好多阳光从房顶上漏下来,星星点点落在她身上。我伸手去触她的乳头,直到她脸上泛起红晕,乳房坚挺。忽然她从迷梦里醒来,羞得满脸通红。于是她紧紧地抱住我。
当我沿着一条路走下去的时候,心里总想着另一条路上的事。这种时候,我心里很乱。
那一夜开头有月光,后来月亮落下去,出来一天的星星,就像早上的露水一样多。那天晚上没有风,山上静得很。我已经和陈清扬做过爱,不再是童男子了。但是我一点也不高兴。因为我干那事时,她一声也不吭,头枕双臂,若有所思地看着我,所以从始至终就是我一个人在表演。其实我也没持续多久,马上就完了。事毕我既愤怒又沮丧。
这是他的似水流年,不是我的。岁月如流,就如月在当空,照着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每个人的生活都不一样。
人活着都是为了要表演,所以才失去了自我。
所谓虚伪,打个比方来说,不过是脑子里装个开关罢了。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必须做出判断:事关功利或逻辑。扳到功利一边,咱就喊皇帝万岁万万岁,扳到逻辑一边,咱们就从大前提,小前提,得到必死的结论。由于这一重担,虚伪的人显得迟钝,有时候弄不利索,还要犯大错误。
我听见浩浩荡荡的空气大潮从我头顶涌过,正是我灵魂里潮兴之时。正如深山里花开,龙竹笋剥剥地爆去笋壳,直翘翘地向上。到潮退时我也安息,但潮兴时要乘兴而舞。
案发时的情形是这样:陈清扬骑在我身上,一起一落,她背后的天上是白茫茫的雾气。这时好像不那么冷了,四下里传来牛铃声。这地方的老傣不关牛,天一亮水牛就自己跑出来。那些牛身上拴着木制的铃铛,走起来发出闷闷的响声。一个庞然大物骤然出现在我们身边,耳边的刚毛上挂着水珠。那是一条白水牛,它侧过头来,用一只眼睛看我们。
“好吃懒做、好色贪淫是每个人的本性,假如你做到克勤克俭,守身如玉,就犯了矫饰之罪,会比好吃懒做、好色贪淫更可恶。”
细的尘土,好像一层爽身粉。我一生经历的无数次勃起,都不及那一次雄浑有力,大概是因为在极荒僻的地方,四野无人。我爬起来看牛,发现它们都卧在远处的河汊里静静地嚼草。那时节万籁无声,田野上刮着白色的风。河岸上有几对寨子里的牛在斗架,斗得眼珠通红,口角流涎。这种牛阴囊紧缩,阳具直挺。我们的牛不干这种事。任凭别人上门挑衅,我们的牛依旧安卧不动。为了防止斗架伤身,影响春耕,我们把它们都阉了。
犯不着向人证明我存在
我始终盼着陈清扬来看我,但陈清扬始终没有来。她来的时候,我没有盼着她来。
漫山冷雾时,腰上别着刀子,足蹬高统雨靴,走到雨丝里去。但是同样的事做多了就不再有趣。所以她还想下山,忍受人世的摧残。
一只蜥蜴从墙缝里爬了进来,走走停停地经过房中间的地面。忽然它受到惊动,飞快地出去,消失在门口的阳光里。这时陈清扬的呻吟就像泛滥的洪水,在屋里漫延。我为此所惊,伏下身不动。可是她说,快,混蛋。还拧我的腿。等我“快”了以后,阵阵震颤就像从地心传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随着医学的发展,干点缺德事不要紧,生孩子没屁眼可以做人工肛门,怕什么?
别让别人注意到你。
在章风山她骑在我身上一上一下,极目四野,都是灰蒙蒙的水雾。忽然间觉得非常寂寞,非常孤独。虽然我的一部分在她身体里摩擦,她还是非常寂寞,非常孤独。后来我活过来了,说道:换换,你看我的。我就翻到上面去。她说,那一回你比哪回都混蛋。
我和陈清扬在蓝黏土上,闭上眼睛,好像两只海豚在海里游动。天黑下来,阳光逐渐红下去。天边起了一片云,惨白惨白,翻着无数死鱼肚皮,瞪起无数死鱼眼睛。山上有一股风,无声无息地吹下去。天地间充满了悲惨的气氛。陈清扬流了很多眼泪。她说是触景生情。
我心中的怪诞——我。
陈清扬后来说,她始终没搞明白我那个伟大友谊是真的呢,还是临时编出来骗她。但是她又说,那些话就像咒语一样让她着迷,哪怕为此丧失一切,也不懊悔。其实伟大友谊不真也不假,就如世上一切东西一样,你信它是真,它就真下去。你疑它是假,它就是假的。我的话也半真不假。但是我随时准备兑现我的话,哪怕天崩地裂也不退却。就因为这种态度,别人都不相信我。我虽然把交朋友当成终身的事业,所交到的朋友不过陈清扬等二三人而已。
好危险,差一点爱上你。
我们俩吵架时,仍然是不着一丝。我的小和尚依然直挺挺,在月光下披了一身塑料,倒是闪闪发光。
陈清扬说,在此之前二十多年前一个冬日,她走到院子里去。那时节她穿着棉衣,艰难地爬过院门]的门槛。忽然一粒砂粒钻进了她的眼睛。这是那么的疼,冷风又是那样的割险,眼泪不停地流。她觉得难以忍受,立刻大哭起来,企图在一张小床上哭醒。这是与生俱来的积习,根深蒂固。放声大哭从一个梦境进入另一个梦境,这是每个人都有的奢望。
“黄瓜愿意开一朵花,就开一朵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愿意结个大的就结个大的,愿意结个小的就结个小的。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
寂寞的城市里开了一串串寂寞的灯光,鸢尾再绚烂也只是寂寞地开放。不眠的灯光只照着失眠的人,而空虚的生活又能有多漂亮?
我这个人,一向不大知道要脸。不管怎么说,那是我的黄金时代。虽然我被人当成流氓。我认识那里好多人,包括赶马帮的流浪汉,山上的老景颇等等。提起会修表的王二,大家都知道。我和他们在火边喝那种两毛钱一斤的酒,能喝很多。我在他们那里大受欢迎。除了这些人,猪场里的猪也喜欢我,因为我喂猪时,猪食里的糠比平时多三倍。然后就和司务长吵架,我说,我们猪总得吃饱吧。我身上带有很多伟大友谊,要送给一切人。因为他们都不要,所以都发泄在陈清扬身上了
凡人都要死。皇帝是人,皇帝万岁。还有:人都要死,皇帝是人,皇帝也会死。很明显,这个世界里存在两个体系,一个来自生存的必要,一个来自生存的本身,于是几乎每一个问题同时存在两个答案。这就叫虚伪。
存在本身有无穷的魅力,为此值得把虚名浮利全部放弃
那年我21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人生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
那一天我21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会一天天消失。
“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忍受摧残,一直到死。想明白了这一点,一切都能泰然处之。”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逝,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