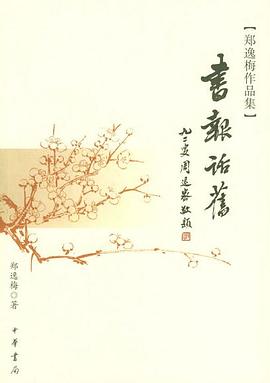内容简介
狐狸不属于野兽,不属于我们人类,也不属于神灵。
她是一个永恒的偷渡者,一个在世界之间穿梭自如的移民,被抓到逃票时,就会用尾巴玩球,表演她廉价的小把戏,目光极为短浅地将观众转瞬即逝的赞叹当成了爱。那是她的荣耀时刻。
其他的一切都是恐惧的历史:逃避猎人的子弹、不停狂吠的猎犬 、迫害、殴 打、舔舐伤口、羞辱、孤独和廉价的安慰——一串鸡骨头做的手摇铃。
狐狸是作家的图腾。
编辑推荐
★ “你从未听说过的十个伟大的作家之一”
南斯拉夫NIN奖、奥地利国家欧洲文学奖、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得主长篇力作
《出版人周刊》《柯克斯评论》《新政治家》2018年度最佳图书、入选国际布克奖短名单
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1949年生于前南斯拉夫,内战爆发后流亡欧洲,一生反对战争及民族主义,致力于推动母语的开放性,维护文化的连续性。她坚持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写作,但拒绝承认自己是克罗地亚作家,而是将自己定义为“跨国界”或“后-国家”的写作者,并于 2017年参与签署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黑及黑山知识分子及公众人物联合发起的《共同语言宣言》。
以自身经验为源泉,杜布拉夫卡多年来一直在书写“故国”“战争”“移民”“流亡”“同胞”,但她不甘于只做时代的记录者和见证人,不断深入“语言”与“叙事”内部,探索人类心灵的幽微角落与群体命运的无常瞬间,以复杂的结构、有力的意象、准确的修辞,将“历史”与“记忆”妥帖地安放在“文学”的世界,呈现了一种极具反思能力的移民文学样本,同时也是一部绵延无尽的命运组曲。
杜布拉夫卡长年盘踞诺奖赔率榜前列,同时也是欧洲极为重要的知识分子型作家,《卫报》赞称杜布拉夫卡是“你从未听说过的十个蕞伟大的作家之一”,苏珊·桑塔格对她也极为珍视:“一个值得被仿效的作家。一个应当被珍惜的作家。”约瑟夫·布罗茨基更是不吝赞美:“看清这个世界的黑暗需要一双局外人的眼睛: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就是那个局外人。”
★ 一个“故事之为故事”的故事
命运如纷飞的雪花,彼此粘连,相互附着;叙事如滚动的雪球,层层覆盖,重重掩饰。
全书分为六个部分,也可视作六部交相影绰的中篇,但最终,看似毫不相关的人物命运彼此互文,密度极高的文本碎片层层嵌套,推演出“讲故事”这门古老技艺的核心秘密——
“真正的文学之乐始于故事逃脱作者控制的时刻,这时它开始表现得像一个旋转的草坪洒水器,朝四面八方喷射;这时草开始萌芽,不是因为任何水分,而是因为对附近水分的渴求。”
“说来说去,一个好故事的秘密究竟在哪里?在光与影、隐藏与袒露、言说与沉默的交错中?或是用形式主义者的话来说,在材料的组织中?更何况:是我选择了皮利尼亚克的故事,还是皮利尼亚克的故事选择了我?我讲述的是皮利尼亚克的故事,还是我自己的故事?无论结局如何,皮利尼亚克的故事讲的不也是我吗?!皮利尼亚克的故事所蕴含的启示是不断变幻的还是一成不变的?读者和译者在故事的形成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对于皮利尼亚克的故事而言,我是个破坏者还是共同创作者?皮利尼亚克的故事材料对于我的价值,是否等同于索菲亚的简短传记和田垣的小说对于皮利尼亚克的价值?更有甚者,相当于索菲亚对于田垣的价值?”
★ 一部写给“文学脚注”的传记
献给与成千上万个外省女孩别无二致的索菲亚、由狐狸取走头颅放在刺猬脚下的作家皮利尼亚克、被纳博科夫用来命名新品种蝴蝶的多萝西、“我”的母亲、寂寂无名的俄罗斯先锋派儿童文学作家列文及其遗孀……
人的一生不过是一系列脚注。我们都是脚注。文学脚注像训练有素的斗鸡一样为生存而战,在某个时刻决胜出谁把谁变成脚注,谁为谁作注,谁是文本而谁是脚注。我们都是行走的文本,我们穿行在世界上,身上粘着看不见的副本,那是我们自身的无数个修订版,但我们对它们的存在、数量和内容一无所知。我们用肉体承载着其他人的经历,而对这些人,我们同样一无所知。我们彼此粘连,像写着层层隐藏文字的透明纸页,我们所有人都生长进彼此,每个人都被秘密的漫游者独自栖居着,而我们,也栖居在别人家里。
★ 一份永远“烧不毁的手稿”
“世界是一片雷区,也是我们唯一的家。”
“历史像嗑南瓜子一样无情地蚕食着人类的生命,留下了一堆又一堆空壳。”——
重要的是文本留了下来。就列文而言,留下的不是文本,而是文本的缺失,是一个洞,一个哈欠,一个能激发想象的苍白轮廓。文本的缺失、形象的缺失、音乐的缺失,是奖章的背面,也是时代的象征。文本的缺失闪耀着神奇的光芒,它跳动着,丝毫不失真实和生动。多伊夫伯·列文的故事不是真实艺术协会对官僚文化趣味的咒骂,也不是对假装恒定的制度的咒骂。那是一种形而上的咒骂(无论这听起来有多荒谬),它展示了想象和创造的力量如何超越了语言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手稿的确是烧不毁的。
★ 一种乡村杂耍般的当代文学娱乐现场
“在皮利尼亚克生活的时代,文学语言强大且处于支配地位,影像年轻而令人兴奋。而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文字已经被挤到了角落里,我们怎能指望那些新技术的使用者,那些身体与精神都经历了蜕变、以图像和符号为语言的人,去阅读不久之前还被称为文学作品,现今则被泛泛称作书的东西呢?” ——
对于页数的敬畏,太过轻易地变成了一个美学范畴,其中也包括对超产作家的崇拜;还有那些投注文学奖的赌徒呢?所有这些都更接近韧性、膂力以及马戏团猛男的范畴,而不是传统的美学范畴;再比如说所谓的实验文学,在今天意味着古怪离奇的主题,一份文学稿件与其说是文学技巧、观念和知识的产物,毋宁说是份病例。现代主义关于实验文学的概念和今天非常不同。如今的实验文学相当于小矮人、大胡子女士、橡皮人等怪咖秀。马戏团表演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艺术方案,它仍然保留在我们许多人的文化记忆中。随着学术性美学裁决的消失,随着所有重要艺术理论的死亡,唯一可以用来区分艺术作品和非艺术作品的指南针,就只剩最接近艺术原初理念的东西,也就是马戏团的表演。再说说文学节这个流行的文学娱乐形式。在每个欧洲国家,每年都有十几个国际文学节。如今的文学节和中世纪的乡村集市并没有什么不同,赶集的人从一个摊位溜达到另一个摊位,看完吞火表演再看杂耍。如今的作家不再让读者通过阅读背上重担,相反他们是在表演。观众的接受标准是被电视和网络训练出来的,他们对文学变得越来越无知,他们想要的只有快速、明确的娱乐……
★ 一种“数字古典主义时代”的文学信念
“文学经典将以动画电影、虚拟现实、电脑游戏等媒介最快、最有效地传递给未来的人……最终,未来的时代将被称为数字古典主义的时代。” ——
故事不会自己讲出来,就像镜子无法变成湖泊,梳子无法变成茂盛的草丛,没有与严肃的危险相连的深刻冲动,梭子鱼的命令也不会成真。(谁知道呢?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小姑娘不小心说出了错误的命令,即“故事,设定你自己!”,而不是“故事,讲出你自己!”)只有当人们不滥用咒语时,魔法才会奏效。因此,在每一个故事里,哪怕是童话故事里,尤其是童话故事里,都必须有一种更高的真实性成分(务必不要把这里的真实性与真实、说服力、人生经验或道德混淆),否则故事就无法运转。一定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能解释,为什么这个故事、这个特定的故事,不得不被讲出来。狐狸知道书中的每一个诀窍,但这依然不够。然而,当生存成为问题时—就像故事中那个可怜的男人把狐狸皮偷来放在家中做妻子—狐狸便会放弃所有谈判的努力,回归它真实的自我。“不可滥用上帝之名”,只有当我们承认这句话的时候,上帝才真正存在。如果我们不相信文学的神奇之处,那它就只是一串毫无意义的文字。
内容简介
凭借着独特的智慧和叙事的力量,杜布拉夫卡带领我们从俄罗斯穿越到日本,从巴尔干雷区到美国的公路,从1920年代到当下,探索了叙事和文学创作的动力、移民的身份与处境、女性及其写作、战争后遗症、当今时代文学的处境等诸多命题。全书分为六章,在历史和地域之间交织跳跃,却信手拈来,游刃有余。杜布拉夫卡以各个文化中古老神话都具备的“狐狸”为原型,逐层揭示了“故事之为故事”的奥秘。
......(更多)
作者简介
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Dubravka Ugrešić,1949—2023),克罗地亚裔荷兰籍作家,出生于前南斯拉夫,在萨格勒布大学就读期间,主修俄语文学及比较文学,并开始文学创作,毕业后留校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工作,于1981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91年,南斯拉夫内战爆发,杜布 拉夫卡因公开反对战争及民族主义,遭到国内舆论的猛烈攻击,于1993年被迫离开克罗地亚。此后,杜布拉夫卡先后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1996年定居荷兰阿姆斯特丹,从事小说创作、文化评论、翻译、文学研究及编辑出版等工作,致力于推动母语的开放性,维护文化的连续性。
著有《渡过意识之流》(Fording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谎言文化》(The Culture of Lies)、《无条件投降博物馆》(The Museum of Unconditional Surrender)《多谢不阅》(Thank You for Not Reading)、《疼痛部》、《Baba Yaga下了一个蛋》(Baba Yaga Laid an Egg)、《狐狸》等作品,已被翻译为三十多种语言,获南斯拉夫NIN奖、奥地利国家欧洲文学奖、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获国际布克奖提名,入围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短名单。
杜布拉夫卡坚持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写作,但拒绝承认自己是克罗地亚作家,她将自己定义为“跨国界”或“后-国家”的写作者,并于 2017年参与签署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黑及黑山知识分子及公众人物联合发起的《共同语言宣言》。
⭐️译者简介
刘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自由译者、撰稿人。译有詹姆斯·索特《这一切》。
......(更多)
目录
读书文摘
柯隆芭:啊,他生病卧床?!我母亲对我说过,我不能单独跟一个男人呆在放有一张床的房间里。 柯尔威诺:让你妈去见魔鬼的母亲吧!
最好他作为贵族公子,跟她尝试阿雷廷诺的三十八幅铜版画描绘的种种方法……
这些狡猾的影子用尾巴尖儿旋转着球,它们是娴熟的杂耍者,诡计多端的人,是移形大法者、骗术大师和幻象家,是一条、三条、五条尾巴的狐狸……这些狡猾的影子在天空中漂浮,如同发光的星体,蓝光闪烁如炸开的烟花。
以某个全球文学明星为例,他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顿悟时刻是如何在一场棒球比赛中到来的。就在球飞过空中的那一刻,他意识到他要写一部小说。所以一回到家,他就坐在书桌前拿起了笔,就此声名鹊起。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