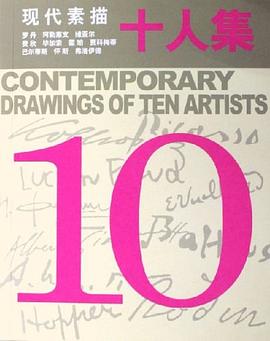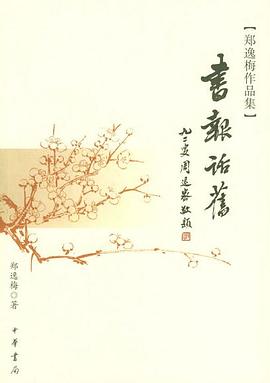内容简介
......(更多)
作者简介
......(更多)
目录
......(更多)
读书文摘
不管天气多热,姐姐仍然吞噬着刚刚做好的、烫嘴的葡萄柚果酱,她大口大口地吞下去,从不细细品味。她低着头的侧脸,看上去很哀伤,仿佛在鸣咽。为了不让眼泪流出来,她一刻不停地一勺勺往嘴里送果酱。越过姐姐望向院子,绿色植物都被太阳晒得打了蔫。我们周围的蝉鸣一直没有间断。
从那些裂缝里溢出了蜂蜜,蜂蜜像血液一样黏稠,静静地流淌着。 我听着嗡嗡声,眺望着眼前的蜂巢,想起了沉睡着的助骨扭曲的先生,有着美丽左手的失踪的学生,用完美的肩胛骨击球的表弟。一个一个,他们好像都被慢慢地吸入学生宿舍的某个无底洞里去了。我朝蜂巢伸出手,迫切地想要住他们。蜂蜜在我的手指够不到的地方一刻不停地流着。
在我看来,夫妻就像是某种不可思议的气体,犹如那种既无轮廓、又无颜色的锥形烧瓶的透明玻璃般的变幻无常的气体。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