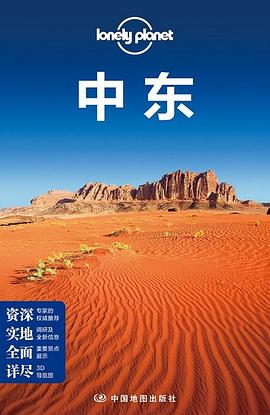内容简介
◆《蝴蝶梦》是成名作,《浮生梦》是巅峰代表作。
◆因为爱你,我变成了一个疯子。
◆如果我拥有整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也属于你!
◆BBC百部英国人最爱文学经典!
◆相比于《蝴蝶梦》,我更偏爱《浮生梦》。 ——金庸
◆《蝴蝶梦》作者感动全球亿万读者的最炽热初恋故事。
+++++++++++++++++++++++++++++++++++++++++++++++++++++ ++ ++++
我使劲想,我还能给她什么东西。
她有了家产,有了钱,有了珠宝。
她还拥有我的思想、我的身体,以及我的心。
抚养菲利普长大的堂兄突然去世了,他的妻子也从意大利来到了英国。菲利普宁静的乡间生活就是在第一眼见到她时被毁掉的。瑞秋俘获了他的心。他不知道的是,对瑞秋的迷恋,很快就会将他推入自我毁灭的边缘。在他为这份感情奋不顾身的同时,他也将所有人的命运推向了一个无法逆转的方向。
+++++++++++++++++++++++++++++++++++++++++++++++++++++++++++++
媒体评论:
◆相比于《蝴蝶梦》,我更偏爱《浮生梦》。 ——金庸
◆和《蝴蝶梦》是同一类故事,但故事的讲述更加完美!——《卫报》
◆在当下这个时代,无论是对读书的人,还是写作的人,这本书的出版都是一则好消息。 ——《狼厅》作者,布克奖得主 希拉里•曼特尔
◆英国现代经典作品中最好的作品之一。
——普利策奖得主,美国儿童文学作家 艾莉森•卢里
◆纯文学高度的经典作品,丰富了所有阅读者的眼界。没有这部作品的图书馆是不完整的。 ——英国当代畅销小说作者 乔安娜•特罗洛普
◆从第一页开始,读者就被迅速带进了《蝴蝶梦》中曾呈现出来的阴森压抑的氛围中。 ——《纽约时报》书评版
◆英国小说家中,没有一个能够做到像杜穆里埃这样打破通俗小说与纯文学的界限,让自己的作品同时满足这两种文学的共同要求。 ——E.M.福斯特
◆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出版物中,这是最好的也是最有存在价值的作品之一。
——英国当代畅销作家 阿莉•史密斯
......(更多)
作者简介
达芙妮•杜穆里埃(Daphne du Maurier,1907 - 1989)
全世界的图书馆里被借阅次数最多的女作家。英国当代著名女作家,英国皇家文学会会员。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世界级作家之一。
杜穆里埃一生共创作有17部长篇以及几十种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 被誉为“打破通俗 小说与纯文学界限”的大师级作家。1938年出版的成名作《蝴蝶梦》甚至影响了一个时代情感小说的走向。其巅峰时期的代表作《浮生梦》则以英国西南部风土人情为背景,刻画了一个炽热感伤的唯美爱情故事,被评论界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好也是最有存在价值的作品之一”。
达芙妮•杜穆里埃一生精彩传奇。她出生文学世家,祖父乔治•杜穆里埃是作家和插图画家,父亲杰拉尔德•杜穆里埃爵士是著名的戏剧演员。她从小就深受文学和戏剧的熏陶。她的父亲有三个女儿,达夫妮希望自己是个儿子,以满足父亲的期望。终其一生,她自视为男性,使自己的女性生活隐含了压抑着的冲突,不过她隐藏了这种感情,只在文字中显示自己的内心冲突。
达芙妮厌恶城市生活,长期住在英国西南部的康沃尔郡,康沃尔郡的生活方式保留了很多维多利亚时代的特征,也是写作哥特式小说的最好土壤。她的小说多以当地农庄的社会习俗与风土人情为主题或背景,崇尚原始生活,充满浪漫感伤的情调,人物刻画细腻,情节曲折,气氛神秘,夹杂着带有宿命论色彩的感伤主义。
译者简介:
姜秋霞
教授,翻译学博士,英语教学论博士生导师,曾任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现任兰州城市学院副校长,译作有《夜访吸血鬼》《浮生梦》等。
......(更多)
目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9
第三章 21
第四章 33
第五章 46
第六章 55
第七章 66
第八章 83
第九章 96
第十章 106
第十一章 118
第十二章 131
第十三章 146
第十四章 162
第十五章 175
第十六章 188
第十七章 202
第十八章 214
第十九章 227
第二十章 239
第二十一章 256
第二十二章 273
第二十三章 292
第二十四章 309
第二十五章 321
第二十六章 342
......(更多)
读书文摘
“你看到了,菲利普,”他说,“这就是我们所有人最终的结局,有的人死在战场,有的人死在床上,各人命运不同,但都难免一死,你不可能太早懂得这些道理。但这是犯罪的下场,它对你、对我都是一种警告,告诉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有节制地生活。”
我们只是梦想者,我们俩都是,不切实际,矜持内向,充满从不加以证实的理论,世界清醒,而我沉醉。我们渴求激情,然后羞怯的天性压抑着冲动。直到心灵被触动时,才觉得天国的大门已为我们打开,感到我们拥有宇宙间所有的财富。
我轻声念出她的名字,听起来是那么温柔悦耳。它在舌尖徘徊,既充满诱惑,又步履缓慢,仿佛毒药一般,这么说也算恰如其分。它从舌尖传递到干裂的唇边,再从唇边移到心口,心掌控着身体,也掌控着思想。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口,拉开厚重的窗帘,凝视着窗外的草坪,静默了好一阵。寂静无声的傍晚,穴鸟已经归巢,猫头鹰已不再啼叫。“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们把小路都挖了,种上了草,现在屋前都是草地,”他说道,“如果草地一直延伸到斜坡那头的马厩旁,效果可能会更好。什么时候你再把那些灌木处理掉,就可以一眼望到海了。”“你这话什么意思?”我说,“干吗是我来处理,而不是你?”他没有马上回答我的疑问。“一回事,”他最后说道,“这是一回事,没什么区别。你可得记着做啊。”
真是天意不测,命运难料。你和我这么亲,大概能揣测这几个星期我内心的骚动。骚动这个词用得不对,也许应该说是从幸福的迷茫到最终下决心的过程。我并没有仓促决定,你知道,我是一个刻板的男人,不会一时兴起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然而几个星期前,我知道了没有其他路可走,我发现了一些从没有过的,甚至曾经认为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即便现在,我还难以相信这一切已经发生了。
我们穿行于狭窄拥挤的街道,一路上随着他的吆喝声和马车的叮当声,人群不断地闪过,钟声慢慢地消失,但余音仍在我耳畔回响,然而这庄严嘹亮的钟声,既不是为我这次无足轻重的远行而响,也不是为了这街上人的生活而响,而是为了永恒,为了不朽。
每当我准备坐车去伦敦时,总是脸色煞白,眼泪汪汪的,而他总会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没事,这是一种训练,就像驯马一样。我们谁都逃不过这一天,这个假期过去了,下一个假期转眼就到,到时候我就接你回来,就哪儿也不去了。我自己来训练你。”“训练我什么呢?”“嗯,你是我的继承人,不是吗?这里面是有学问的。”于是,我就走了。
我叫他别犯傻了,没有他,安布鲁斯和我会过得一团糟。可他却摇摇头,板着个脸不停地在原地来回踱步,而且不失时机地对未来作出种种凄苦的假设:什么就餐时间毫无疑问要改啦,家具要换啦,什么大家伙儿会被呵斥着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打扫房间啦,最可怕的是,连那几条可怜的狗也会被拖垮。他就这样用一种近乎于悲哀的声音絮絮叨叨着种种未来的情景。不过,他的这种腔调倒多少帮我找回了一些失去的幽默感,自从读了安布鲁斯的信以来,这是我第一次放声大笑。
我坐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信,又读了一遍。如果我对那两个在那不勒斯共享幸福的人有一丝同情,一点快慰,哪怕一点点的激动,我的良心都能有些许的安慰。我真为自己感到难为情,想想自己这么自私,内心一点温情都没有,简直是怒不可遏。我坐在那儿,两眼呆呆地望着风平浪静的海水,心中无限悲哀。我刚刚二十三岁,就像多年以前在哈罗第四讲堂的凳子上坐着的时候那样,感到无比的孤独与落寞,身边没有一个朋友,前景一片茫然,只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世家,这个世界里有着我从未有过,也不想有的感受。
“我已逐渐对咱们的表亲瑞秋产生了诚挚的敬意,”安布鲁斯在初春时写来的信上这么说,“而且一想到她跟着桑格莱提那个家伙受的那份委屈,心里着实难过。这些意大利人简直就是一帮无耻的恶棍,这一点毋庸置疑,而她在外貌和行为方式上都和你我一样,俨然一个英国人,就好像昨天还生活在塔默尔似的,只是对家族了解甚少,一切都得我讲给她听。谢天谢地,她绝对机灵,知道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丝毫没有妇道人家常有的喋喋不休的毛病。她帮我在费索勒找了很好的住处,离她的别墅不远,随着天气日渐转暖,我会更多地去她那儿,在阳台上坐坐,或者去花园里逛逛,这些花园的造型和里面的雕塑看上去都是出自名家手笔,不过我不大熟悉。
日复一日,到了第三个冬天,这次他决定去意大利,打算去看看佛罗伦萨和罗马的一些花园。这两个城市的冬天都不暖和,可这对他来说没大要紧的,他并不在意,因为他听说那里虽然很冷,却很干燥,而且他也没必要介意雨水多少。最后一个晚上,我们聊得很晚,他从来都是很晚才睡觉的,我们经常在书房里坐到凌晨一两点。有时说说话,偶尔一句话也不说。那晚我们俩伸展双腿,烤着火,几条狗蜷伏在我们脚边。前面说了,我当时一点预感也没有,可现在回想起来他倒像是有什么预感似的,不时望我一眼,一副若有所思却又十分茫然的神情,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墙壁,看看那些熟悉的画,一会儿又看看火,再看看蜷伏的狗。“真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去!”他突然迸出这么一句。
他的信我都保存着,现在身边有一大捆信件。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这些信被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在我的手里反反复复地摸来摸去,仿佛手指的接触,能使我从中获得比语言更多的内容。就是在寄自佛罗伦萨的第一封信——显然他在那儿过了圣诞节——的结尾处,他首次提到了表姐瑞秋。
再不会有什么问题了,所有这些都是你的,如果我拥有整个世界,那么世界也属于你。
我打了个手势让他等着,便下了车,来到门口,拉了拉墙上的门铃,可以听见里面的铃声。车夫把马车停在路边,然后从车上下来,站在沟渠边,用帽子挥赶着扑面的苍蝇。可怜的马看上去有一些饿了,在车辕间低垂着头,抽动着耳朵,走了这些路之后,它已没有力气到路边去吃青草,而是在一旁打起盹来了。门内没有声音,我又拉了下门铃,这次传来低沉的狗叫声,接着有扇门开了,狗叫声随即清晰起来,能听到一个孩子烦躁的哭声,一个女人呵斥孩子的尖叫声,同时另一边传来走向门口的脚步声,接着是取下门闩的声音和门擦着地下的圆石的声音。门打开了,一位农妇站在我面前,打量我。
我觉得当时最令我感到羞辱的是他的朋友们快乐的神情,他们对他的幸福表现出来的诚挚的喜悦和真切的关心。恭喜之声如潮水般向我涌来,把我当成了给安布鲁斯传递信息的使者。面对这一切,我所能做的只是不断地微笑,点头,装出一副好像我就知道这件事会发生的样子,我感到自己变成了一个双面人,一个背叛者。安布鲁斯一直教我要憎恨虚伪,无论是人的虚伪,还是动物的虚伪。而我现在竟然把自己伪装成了一个与从前的我截然不同的角色,想到这个,我简直痛苦不堪。
我不善于旅行,你就是我的整个世界。
我在轻声念叨她的时候,她的名字听起来是那样的柔和悦耳,久久滞留在唇间,挥之不去,像毒品一样缓缓地、执著地渗透进体内,从舌头滑到干裂的双唇,再从双唇移到心脏,心脏控制了躯体,也控制了大脑。有朝一日,我能摆脱掉它吗?四十年以后,还是五十年以后?或者某种缠绕于脑际的痕迹还会久久徘徊不去?还是流动的血液里某个小细胞不能和其他同伴一起顺利到达心脏?也许,等一切都说了,一切都做了,我也就不再想解脱了。但现在还说不清。
如果我是另外一种人,机灵敏捷,口齿伶俐,又有经商的头脑,那么过去的一年就是另外十二个月的样子了。我会一心向往过一种快乐安逸的生活,很可能会结婚,组成一个年轻的家庭。然而,我根本不是这种人,安布鲁斯也不是。我们只是梦想者,我们俩都是,不切实际,矜持内向,充满从不加以证实的理论,世界清醒,而我沉醉。我们渴求激情,然而羞怯的天性压抑着冲动。直到心灵被触动时,才觉得天国的大门已为我们打开,感到我们拥有宇宙间所有的财富。如果我们是另外一种人,我们俩就都能获得新生。
他就那样被吊在绞架上,在天与地之间荡来荡去,或者用我堂兄安布鲁斯的话说,在天堂与地狱之间荡来荡去。天堂,他永远无法到达;地狱,他也已经进不去了。安布鲁斯用棍子戳那具尸体,当时的情景现在仍历历在目。尸体挂在一个锈迹斑斑的旋轴上,像个风标一样,在风中摇摆,看上去很像一个可怜的稻草人,然而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他的尸体虽还完好,但身上的裤子已因长时间的风吹雨淋而破烂不堪,布条像烂纸片一样挂在肿胀的四肢上。那时正值冬天,不知哪个过路的人寻开心,在尸体的破烂上衣上插了一枝冬青以示祝贺。无论如何,对于七岁的我来说,这简直是极端的暴行,不过我一声没吭。
“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我不断地听到这句话,而且还要随声附和。于是我开始躲避周围的邻居,把自己关在树林旁的家中,免得再看到那些关注的面孔,再听到他们那些喋喋不休的议论。无论去田间还是去镇上,我都无法逃开这一切。庄园里的佃户们,或随处可见的熟人,只要一瞥见我,就会迫使我卷入他们的交谈。我简直成了个蹩脚的演员,脸上努力挤出一丝微笑。这么做的时候,我感觉到皮肤在抵触地抽动,可我不得不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回答他们的问题。我讨厌这种伪装,可是别人希望在提到安布鲁斯的婚事时,看到我这种高兴的样子。
之后,我又收到了他的一两封信,都是些闲言碎语,没什么新鲜事,比如说刚和瑞秋表妹用过餐回去,或者是正准备去她那儿吃饭。他说她那些佛罗伦萨的朋友中,几乎没有人能真正无私地给她出主意,他自诩自己能做到这一点,为此她很感激。尽管她兴趣广泛,但不知何故总是显得很落寞,大概从来就没有能和桑格莱提沟通过,她说她一直渴望有英国人做朋友。“我觉得回家的时候除了能带回几百株植物之外,还能另有所成。”他说。接下来是一大段漫长的日子,他没说什么时候回来,但以往都在四月底前回家。寒冷的冬季好像迟迟不去,西部国家一向有很轻微的霜冻,今年出人意料得严重,有些山茶花已经受了影响。我希望他不要很快回来,免得和我们一起经受风霜雪雨。
马车夫威灵顿赶车送我到波得敏坐去伦敦的车。我回过头,最后看了一眼安布鲁斯。他拄着手杖站在那儿,几只狗围绕在他的身前身后。他眯缝着眼睛看着我,目光中充满了对我确信无疑的理解。他一头浓密的卷发已渐渐变白。看到他向狗打了一声呼哨,转身走进房子,我只觉得喉头一阵哽咽。马车穿过门口的草场,驶出白色的院门,经过一片农舍,车轮压在砾石路面上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马车载着无可奈何的我向学校走去,向远离安布鲁斯的日子走去。
我们爬上漫长弯曲的山路,将佛罗伦萨抛在身后,建筑物也消失在视线之外。周围的一切安静而祥和,那整日对这座城市虎视眈眈的屋墙甚至褐色的土地都不再像先前那么干热了,房屋又焕发出光彩来。或许颜色并不那么亮丽夺目,甚至看不出什么颜色,但太阳的威力散尽之后,余晕照射出的色彩分外柔和,遮天蔽日的柏树在夕阳的余晖映照下墨绿一片。车夫把马车停在一座高墙耸立、庭院深锁的住宅外,回头对我说了声:“桑格莱提别墅。”我终于到了。
我二十五岁生日的前一天——噢,天哪!才几个月以前,像是过了很久——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有一些女人,菲利普,往往是很不错的女人,即使自己没犯错,也会带来灾祸。什么事只要和她们有瓜葛,就会成为悲剧。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给你说这些,可我觉得应该告诉你。”说完就看着我在他面前的文书上签了字。不,不能回头了。那个在生日的前一天站在她窗下的男孩,在她到的第一天站在她门前的男孩,已经不见了,已经远去了,正如当年故作勇敢往绞架上那个死人扔石头的男孩远去了一样。汤姆??吉克恩,一个受尽摧残、面目全非又无人问津的人,这些年来,你是不是满怀怜悯地注视着我?注视着我跑进树林,跑向未来?如果转过头去找你,我看到的不会是带着镣铐摆动着的你,而是我自己的影子。
这就是我们所有人最终的结局,有的人死在战场,有的人死在床上,各人命运不同,但都难免一死,你不可能太早懂得这些道理,但这是犯罪的下场,它对你、对我都是一种警告,告诉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有节制的生活。
在我视野得及的地方,唯见笔墨如流水徜徉,窗外照来半缕斜阳,佛光般落入字里行间。
如果你想回,就回吧。不过不要马上就走,再给我几周时间,让我把这段时间深藏在记忆深处。我不善于旅行,你就是我的整个世界。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