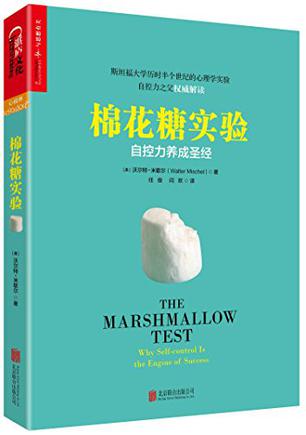内容简介
《恶棍列传》
博尔赫斯首部小说作品,一九三五年出版,讲述世界各地“恶棍”的故事,既有美国南方的奴隶贩子、纽约黑帮头目,也有冒名顶替望族子弟的英国流浪汉,甚至包括日本江户幕府时代侮辱赤穗藩主而最终被复仇的礼官吉良上野介、中国清朝的女海盗郑寡妇。真实的历史背景,与作者的想象交织在一起,刻画出芜杂的社会角落里生长出来的一个个“反英雄”形象。
《小径分岔的花园》
小说集,一九四一年出版,收短篇小说七篇。其中,《小径分岔的花园》是博尔赫斯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为“侦探小说,读者看到一桩罪行的实施过程和全部准备工作”。间谍余准,一路躲避英国军官的追踪,潜入汉学家艾伯特家中。他与艾伯特大谈一部名为《小径分岔的花园》的杂乱无章的小说手稿,突然开枪杀死了艾伯特,借此成功将情报传递给了德国人。“小说—花园—迷宫”的脉络第一次出现在博尔赫斯的作品中,并成为其艺术的关键词。对时间或平行或背离或汇合或交错的不同序列的理解融入写作,无穷的可能性由此而生。
《杜撰集》
小说集,收短篇小说九篇,一九四四年与《小径分岔的花园》合为《虚构集》出版,延续虚构的传奇故事题材。其中作者声称“最得意的故事”的《南方》,被视作博尔赫斯写作的转折点。主人公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立图书馆的秘书达尔曼在上楼时前额莫名地被什么东西刮破,竟至高烧不已,噩梦不断,住进了疗养院,病情好转后他决定回祖辈留下的南方庄园休养,他一路坐出租马车、乘火车、步行,最后临时起意走进一家杂货铺吃饭,却卷入一场决斗,死在对手刀下。这个故事在博尔赫斯的语言迷宫里,又有另外的读法:达尔曼没有死,回南方庄园的旅程其实是他躺在病床上做的梦,他在梦中死于决斗,一个庸常生活中的人在梦中选择了他所向往的轰轰烈烈的死亡方式。
《阿莱夫》
小说集,一九四九年出版,收短篇小说十七篇。阿莱夫()是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数学中代表无穷数、无限的集合,神秘主义理解为超越时空极限的潜在的能量。博尔赫斯以小说的形式展开对时间、对空间、对宇宙、对宏观与微观的思考。在爱慕的女人去世之后,“我”每年仍在她生日那天去她家拜访,她的表哥达内里多年来一直在写一部题为《大千世界》的长诗,他向“我”吐露了一个秘密,地下室角落里有一个“阿莱夫”,那正是他写诗天赋的源泉。“我”静静躺在幽暗地下室的砖地上,眼睛紧盯楼梯第十九级台阶,终于,我看到一个闪烁的小圆球,球里的场景令人眼花缭乱,“宇宙空间都包罗其中”,那就是阿莱夫。
《布罗迪报告》
小说集,一九七〇年出版,收短篇小说十一篇。第三者、告密小人、崇拜驱使之下的复仇、隐秘的决斗……“故事都是现实主义的”,却恍若梦境。所收《布罗迪报告》,从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小说《格列佛游记》得到启发,上呈传教士布罗迪写下的在雅虎人部落生活的报告,报告详尽的细节陈述却营造出一种虚妄之感。博尔赫斯定义明确:“说到头,文学无非是有引导的梦罢了。”
《沙之书》
小说集,一九*年出版,收短篇小说十三篇,博尔赫斯写作后期的*之作。面对一本页码无穷尽的“沙之书”,先开始是据为己有的幸福感,最终领悟是可怕的怪物,是一切烦恼的根源。这本书,是博尔赫斯书籍崇拜情结的体现,象征具有无限性的宇宙、世界。人竭力突破未知,最终却体验到无限而确证自我的渺小无力。“如果空间是无限的,我们就处在空间的任何一点。如果时间是无限的,我们就处在时间的任何一点。”无限性、可能性、死亡、记忆与时间等概念哲学、玄学层面的思考蕴含在各篇当中。
《埃瓦里斯托卡列戈》
随笔集,一九三〇年出版,是博尔赫斯对于阿根廷诗人埃瓦里斯托卡列戈生平和作品的介绍与评价,同时也是他对于阿根廷市井生活的想象。埃瓦里斯托卡列戈是一位根植于市井的诗人,他笔下的市郊,与博尔赫斯的成长环境截然不同,遍布欢声笑语却又随时剑拔弩张。探戈、六弦琴、匕首、英雄、叛徒等等市郊生活的关键词,汇成了博尔赫斯眼中的江湖。
《讨论集》
随笔集,一九三二年出版,收录博尔赫斯所写的书评、影评,展开文学艺术观的讨论。如《高乔诗歌》、《阿根廷作家与传统》关注阿根廷本土文学风貌,《另一个惠特曼》、《福楼拜和他典范的目标》则把目光转向世界文学,《阿喀琉斯和乌龟永恒的赛跑》、《乌龟的变形》探讨作者心心念念的哲学命题。文章涉猎广泛,博尔赫斯说:“我的生活缺乏生命和死亡。正是这种缺乏使我勉为其难地喜好这些琐碎小事。”
《永恒史》
随笔集,一九三六年出版,收八篇。其中《永恒史》梳理并否定了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神学关于“永恒”的历史,《评注两则接近阿尔莫塔辛》试图证实时间的“圆形”性质……“永恒”、“轮回”、“循环”,均指向时间命题。
《探讨别集》
随笔集,一九五二年出版,收三十五篇,是博尔赫斯对他钟爱的作品、钟爱的作家的评论。他由秦始皇焚书谈儒家经典的流传,在卡夫卡的小说里追踪卡夫卡的美学先驱,从济慈的诗句中找寻个体与群体的时空联系,从霍桑和爱伦坡那儿发现幻想与真实相碰撞的心理轨迹,这些不囿成见的审美认识显示出超前的感知。
《诗艺》
演讲集。一九六七年秋,博尔赫斯应哈佛大学诺顿讲座之邀,就诗的地位、隐喻模式、小说与诗、音韵与翻译等展开六讲。讲座录音带在图书馆尘封三十多年后,由时任西安大略大学现代语言文学系副教授的凯林–安德米海列司库整理出版。全集广征博引,涉及从古至今诸多文学现象,又有着口语化文本的不拘形式感,娓娓道来,收放自如。“《诗艺》是一本介绍文学、介绍品位,也介绍博尔赫斯本人的书……博尔赫斯跟历代的作家与文本展开对话,而这些题材即使是一再反复引述讨论也总还是显得津津有味。”
《序言集以及序言之序言》
序言是博尔赫斯钟爱的一种体裁,他写过的序言数以百计。序言也是博尔赫斯锐意革新的一种体裁,他为此专门撰写了《序言之序言》,直言“在微弱多数的情况下,序言近似于酒后的致辞或者葬礼的悼词,不负责任地极尽夸张之能事,读之令人怀疑”,并提出序言的新理论,宣称序言应该是评论的新侧面,而非祝酒词的次要形式。
本书以《序言之序言》为先导,共收录了三十九篇精彩纷呈的序言,评介的对象不受时间空间的羁绊,不仅可以看到作者熟悉的到阿根廷作家,也不乏莎士比亚、卡夫卡、惠特曼等不朽的经典,充分展现了博氏序言的独特风格。
《博尔赫斯,口述》
演讲集。一九七八年五六月间,博尔赫斯在阿根廷贝尔格拉诺大学讲授了五堂课,分别以书籍、不朽、伊曼纽尔斯威登堡、侦探小说以及时间为题。主题看似宏大抽象,作者另辟蹊径,带给读者全新的思辨体验:从口述传统角度谈论书籍的历史,以诗歌为切入点分析不朽的意义,借斯威登堡谈生与死的哲学命题,把侦探小说誉为混乱文学时代里的拯救者。五堂课统以“时间”这个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贯穿始终。
《七夜》
博尔赫斯技巧精湛的写作背后,支撑着的是庞杂浩瀚的阅读量和毕生埋首的治学热情,他的非虚构作品充满了各式各样天马行空的文学动机。本书为演讲集,一九八〇年出版,收录博尔赫斯在一九七七年夏天所做的七场讲座内容,分别以《神曲》、梦魇、《一千零一夜》、佛教、诗歌、犹太教神秘主义以及失明为题,讲述博尔赫斯与《神曲》的交往、镜子与迷宫混杂的梦魇、东方意识、佛教的本质、诗的审美、圣书的观念以及艺术的工具等等。
《但丁九篇》
但丁的《神曲》是博尔赫斯钟爱的作品,本书收录了他为它写下的九篇妙趣横生的短文。本书有别于艰涩乏味、空洞无物的学术论文,有的从《神曲》里的一个人物,有的从其中的一个细节,有的甚至从某个词语出发,结合心理学、哲学、神学等各领域的观点,丰富了对《神曲》的解读。书中没有任何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文学理论和长盘累牍的方法论,每一篇都精致可爱,独立成章,体现出作者极高的文学造诣和阅读素养。
《私人藏书:序言集》
博尔赫斯另辟蹊径,不以文学的运动、年代以及对作品的繁琐分析为标准,而是回归本质,着眼于“文学的美”,精心挑选出自己“爱不释手并极想与人分享的书”,组成一套带有强烈个人风格的“私人藏书”,并为每本藏书作序。本书共收序言六十四篇,一九八八年出版。所论既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家名作,如马可波罗《行纪》、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和《一千零一夜》,也有如今已凐没无闻的拉美作家;既有欧美文坛的巨擘,也有来自日本、印度等东方国家的著作。
......(更多)
作者简介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1986)
阿根廷诗人、小说家、评论家、翻译家,西班牙语文学大师。
一八九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少年时随家人旅居欧洲。
一九二三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一九二五年出版第一部随笔集《探讨集》,一九三五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恶棍列传》,逐步奠定在阿根廷文坛的地位。代表诗集《圣马丁札记》、《老虎的金黄》,小说集《小径分岔的花园》、《阿莱夫》,随笔集《永恒史》、《探讨别集》等更为其赢得国际声誉。译有王尔德、吴尔夫、福克纳等作家作品。
曾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文学教授,获得阿根廷国家文学奖、福门托国际出版奖、耶路撒冷奖、巴尔赞奖、奇诺德尔杜卡奖、塞万提斯奖等多个文学大奖。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四日病逝于瑞士日内瓦。
......(更多)
目录
《小径分岔的花园》(节选)
“我得逃跑,”我大声说。我毫无必要地悄悄起来,仿佛马登已经在窥探我。我不由自主地检查一下口袋里的物品,也许仅仅是为了证实自己毫无办法。我找到的都是意料之中的东西。那只美国挂表,镍制表链和那枚四角形的硬币,拴着鲁纳伯格住所钥匙的链子,现在已经没有用处但是能构成证据,一个笔记本,一封我看后决定立即销毁但是没有销毁的信,假护照,一枚五先令的硬币,两个先令和几个便士,一支红蓝铅笔,一块手帕和装有一颗子弹的左轮手枪。我可笑地拿起枪,在手里掂掂,替自己壮胆。我模糊地想,枪声可以传得很远。不出十分钟,我的计划已考虑成熟。电话号码簿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唯有他才能替我把情报传出去:他住在芬顿郊区,不到半小时的火车路程。
我是个怯懦的人。我现在不妨说出来,因为我已经实现了一个谁都不会说是冒险的计划。我知道实施过程很可怕。不,我不是为德国干的。我才不关心一个使我堕落成为间谍的野蛮的国家呢。此外,我认识一个英国人——一个谦逊的人——对我来说并不低于歌德。我同他谈话的时间不到一小时,但是在那一小时中间他就像是歌德……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觉得头头瞧不起我这个种族的人——瞧不起在我身上汇集的无数先辈。我要向他证明一个黄种人能够拯救他的军队。此外,我要逃出上尉的掌心。他随时都可能敲我的门,叫我的名字。我悄悄地穿好衣服,对着镜子里的我说了再见,下了楼,打量一下静寂的街道,出去了。火车站离此不远,但我认为还是坐马车妥当。理由是减少被人认出的危险;事实是在阒无一人的街上,我觉得特别显眼,特别不安全。我记得我吩咐马车夫不到车站入口处就停下来。我磨磨蹭蹭下了车,我要去的地点是阿什格罗夫村,但买了一张再过一站下的车票。这趟车马上就开:八点五十分。我得赶紧,下一趟九点半开车。月台上几乎没有人。我在几个车厢看看:有几个农民,一个服丧的妇女,一个专心致志在看塔西佗的《编年史》的青年,一个显得很高兴的士兵。列车终于开动。我认识的一个男人匆匆跑来,一直追到月台尽头,可是晚了一步。是理查德马登上尉。我垂头丧气、忐忑不安,躲开可怕的窗口,缩在座位角落里。
我从垂头丧气变成自我解嘲的得意。心想我的决斗已经开始,即使全凭侥幸抢先了四十分钟,躲过了对手的攻击,我也赢得了第一个回合。我想这一小小的胜利预先展示了彻底成功。我想胜利不能算小,如果没有火车时刻表给我的宝贵的抢先一着,我早就给关进监狱或者给打死了。我不无诡辩地想,我怯懦的顺利证明我能完成冒险事业。我从怯懦中汲取了在关键时刻没有抛弃我的力量。我预料人们越来越屈从于穷凶极恶的事情,要不了多久世界上全是清一色的武夫和强盗了,我要奉劝他们的是:做穷凶极恶的事情的人应当假想那件事情已经完成,应当把将来当成过去那样无法挽回。我就是那样做的,我把自己当成已经死去的人,冷眼观看那一天,也许是最后一天的逝去和夜晚的降临。列车在两旁的梣树中徐徐行驶,在荒凉得像是旷野的地方停下。没有人报站名。“是阿什格罗夫吗?”我问月台上几个小孩。“阿什格罗夫,”他们回答说。我便下了车。
月台上有一盏灯照明,但是小孩们的脸在阴影中。有一个小孩问我:“您是不是要去斯蒂芬艾伯特博士家?”另一个小孩也不等我回答,说道:“他家离这儿很远,不过您走左边那条路,每逢交叉路口就往左拐,不会找不到的。”我给了他们一枚钱币(我身上最后的一枚),下了几级石阶,走上那条僻静的路。路缓缓下坡。是一条泥土路,两旁都是树,枝桠在上空相接,低而圆的月亮仿佛在陪伴我走。
有一阵子我想理查德马登用某种办法已经了解到我铤而走险的计划。但我立即又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小孩叫我老是往左拐,使我想起那就是找到某些迷宫的中心院子的惯常做法。我对迷宫有所了解:我不愧是彭冣的曾孙,彭冣是云南总督,他辞去了高官厚禄,一心想写一部比《红楼梦》人物更多的小说,建造一个谁都走不出来的迷宫。他在这些庞杂的工作上花了十三年工夫,但是一个外来的人刺杀了他,他的小说像部天书,他的迷宫也无人发现。我在英国的树下思索着那个失落的迷宫:我想象它在一个秘密的山峰上原封未动,被稻田埋没或者淹在水下,我想象它广阔无比,不仅是一些八角凉亭和通幽曲径,而是由河川、省份和王国组成……我想象出一个由迷宫组成的迷宫,一个错综复杂、生生不息的迷宫,包罗过去和将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牵涉到别的星球。我沉浸在这种虚幻的想象中,忘掉了自己被追捕的处境。在一段不明确的时间里,我觉得自己抽象地领悟了这个世界。模糊而生机勃勃的田野、月亮、傍晚的时光,以及轻松的下坡路,这一切使我百感丛生。傍晚显得亲切、无限。道路继续下倾,在模糊的草地里岔开两支。一阵清越的乐声抑扬顿挫,随风飘荡,或近或远,穿透叶丛和距离。我心想,一个人可以成为别人的仇敌,成为别人一个时期的仇敌,但不能成为一个地区、萤火虫、字句、花园、水流和风的仇敌。我这么想着,来到一扇生锈的大铁门前。从栏杆里,可以望见一条林荫道和一座凉亭似的建筑。我突然明白了两件事,第一件微不足道,第二件难以置信;乐声来自凉亭,是中国音乐。正因为如此,我并不用心倾听就全盘接受了。我不记得门上是不是有铃,是不是我击掌叫门。像火花迸溅似的乐声没有停止。
......(更多)
读书文摘
“你的醒并不是回到不眠状态,而是回到先前一个梦。一梦套一梦,直至无穷,正像是沙粒的数目。你将走的回头路没完没了,等你真正清醒时你已经死了。”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