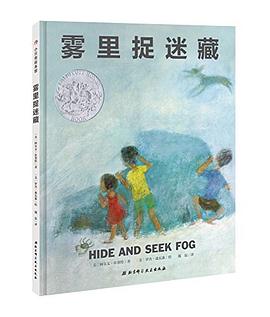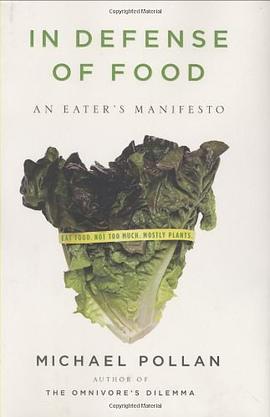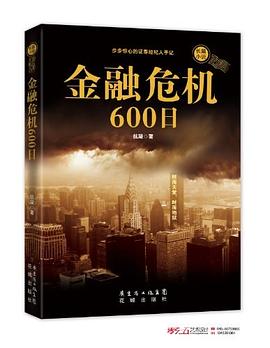内容简介
在近现代之交的中国,梁启超不但名气相当大,而且享名时间长,这在那个“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时代,实属难得。
善于自我剖析的梁启超晚年曾向公众表白:“我的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两样比较,学问兴味更为浓些。我常常梦想能彀在稍为清明点子的政治之下,容我专作学者生涯。但又常常感觉:我若不管政治,便是我逃避责任。”在两种互相冲突、各不相让的兴趣左右与吸引下,梁启超的行动不免彷徨犹疑,视外界形势的变化,而或此或彼,偏重一端;但其内心深处,却始终期望“鱼”与“熊掌”两味兼得,故其人生的最高理想是,“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外交欤?内政欤?》)。且不论政治家与学者这两种社会角色是否可以同时扮演得同样出色,倒是政治兴味与学问兴味的矛盾调适,确是梁启超成名早而又得名久的重要原因。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登上历史舞台的维新派,其当然的精神领袖为康有为。在他随后发起的改良主义政治运动中,梁启超初时不过是作为一名康门弟子随师奔走,宣传康氏的主张。而一旦《时务报》于1896年创刊,他有幸出任该报主笔,便如鱼得水,即刻脱颖而出,显示了其以文字鼓动人心的特殊才干。系列政论文《变法通议》以明白畅达的语言,痛快淋漓地论述了变法势在必行的道理:“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当今之势,是“变亦变,不变亦变”。主动变法,实为“保国”“保种”最明智的选择(《论不变法之害》)。其时,梁启超的思想基本源于康有为,而他以报刊政论家身份所发表的言论,却使其对社会舆论的影响更为普遍,因而一时间声名鹊起,康梁并称,造成了在维新运动中梁氏几与其师平分秋色的态势。
戊戌以前,梁启超对康有为的称扬可谓不遗余力,而政变发生、亡命日本后,他受到现实的刺激——变法失败的打击与日本明治文化的冲击——“思想为之一变”,渐有与康氏分离的倾向。在1898年底于日本横滨创办的《清议报》中,尽管仍接刊《变法通议》的续论二篇,但梁启超思考的中心已不局限于对维新活动本身的检讨,而推及政变发生的远因。1901年发表的《中国积弱溯源论》,其栏目标题为“中国近十年史论”,原拟著成一书,对1894年中日战争以来的历史作一总体清理。首章《积弱溯源论》便放大视阈,对影响近代中国的思想、风俗、政治以及清代史事各种积因逐一阐发,开始关注国民性问题。批判国民性这一思路,在长达十余万言的《新民说》中得到了集中、充分的展现。认识到“国也者积民而成”,“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叙论》),梁启超已从痛恨`顽固派守旧不变,扼杀新政,转而深入探讨更为基本的国民教育问题。通过对国民性的历史批判,倡导培养新国民必备的种种品德,而其最终期望,仍在“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本着这一“开通民智”的新意识,梁启超此时的政论表现出更多责望于国民而不是政府的取向。比较传统的“贤人政治”理想,这应当被视为一种进步。而他于《新民说》中曾力加鼓吹的破坏主义,也应和了革命思潮的传播,引起持君主立宪、保皇改良主张的康有为的不满。“新民”理论的系统阐释,证明梁启超已具有对社会舆论独立发生影响的实力。而连载于1902年创刊的《新民丛报》上的《新民说》及其他以“新民”为主旨的论文,也为梁启超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他的开始于办报活动的政治生涯,在此时期达到了巅峰状态。
1903年以后,康有为的影响再度显现。游历美洲的经历,使梁启超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共和民主制国家颇为失望,考察旅美华人社会的结果,也使他对国民性改造倍感艰难,因此放弃革命、破坏主张,改为宣扬“开明专制论”。而溯其思想转变的伏脉,却与“新民”理论不无关系:国民素质低,固不足以谈革命;而国民觉悟的提高,又有赖于开明君主的干涉、指导。这种议论,与革命派以革命开民智的说法截然对立。由于“新民”理论在现实政治斗争中的保守性,国民性改造问题很快退居其次,被更为紧迫而引入注目的推翻封建专制的革命所取代。同时,梁启超在舆论界的号召力也大为下降。
民国成立,梁启超结束了流亡生活,回到国内。与康有为不同,他并不固执于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而以承认现存国体、谋求改良政体为依据,对共和制度取认可态度。其后,他又以同样的理由,出任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以及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并积极参与了倒袁运动及讨伐张勋复辟之役,在政治立场上与康有为完全分道扬镳。虽勉力于政治事务,比前此以报刊鼓吹政见更切近实际,然而,“理论的政谭家”作为“实行的政务家”原未必合格。梁启超殚精竭虑,可还是发现对于政务家的角色,他并不能胜任。于是,1917年底,他明智地退出了政界,结束了因之成名的政治生涯。
其实,即使在以政论家活动声名最盛的时期,梁启超也始终不曾忘情于学术。少年时代在广州学海堂所接受的旧学训练,一度令其“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三十自述》)。对于国学的兴趣由此培植,并且从未因其后的“舍去旧学”、趋向新学或干政从政而泯灭。一俟政治活动中稍有闲暇,梁启超的治学欲望便不可遏抑地生发。1901年作《中国史叙论》,原是有意撰写一部《中国通史》,然而时势动荡,牵虑政局,梁启超终无余力静心完成这一长篇史著。至1902年写作《新民说》,从历史的深处抉发国民性病源时,对中国旧学的清算也以极大声势展开。《新史学》接续着《中国史叙论》以国民史取代帝王史的思绪,批判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提出新史学的职志,为“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中国之旧史学》《史学之界说》)。在对旧学的重镇——史学进行改造的同时,梁启超还融合西学,以“二十世纪,则两文明(按:指东、西文明)结婚之时代也”的先进眼光,重新阐述与评估中国学术传统,著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为新史学品格的建立提供了范式。不难看出,梁启超此期的学术研究,带有浓厚的现实政治色彩。《新史学》与《新民说》的互相呼应一目了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与其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的诸多论文用心一致,均在求引进西学,融贯中外,催生中国新文明,放大光华于世界,用梁启超的妙喻,即是“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总论》)。其间,最近乎纯学术的著述计划当为《中国通史》,不过,据梁氏自白,其立意也在“助爱国思想之发达”(《三十自述》)。因此,为经世而治学,是政治活动家梁启超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倾向。
以学问为改良政治的手段既被视作理所当然,为学问而学问自然心中不安,偶一涉足,梁启超不免自讼为“玩物丧志”,自觉愧对“国方多难”之时局(《国文语原解·序》)。这种学者型政治家内心矛盾的表露,恰恰证明了学术研究还该有更超然的目的存在。归国之初的梁启超在对大学生发表演说时,即已劝导他们“以学问为目的,不当以学问为手段”,理由是“学问为神圣之事业”,“若于学问目的之外,別有他种目的,则渎学问之神圣”(《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这可以表见暂时脱离政事干扰的梁启超向往学术独立的真实心态。然而,政治兴味甚浓的梁氏,很快又因卷入党派活动而步入政坛,从政论家出为政务家,公文丛集,公事缠身,更无余暇进行完整的学术著述。若仅以此政绩,梁启超殊不足以留大名于现代史。
幸好,于政治宣传之外,梁氏还别有所长。辞去政府职务后,他即埋首于蓄志已久的《中国通史》写作,数月后虽因病中辍,而积稿已十余万言。1918年底出游欧洲,历时一年余。归国当年,便以《清代学术概论》的撰写与面世为标志,显示了其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放弃政治活动,专心研治国学,这一人生路向的转换,也是梁启超重新对社会发生普泛影响的契机。尽管仍不免就时事发表意见,他却谨守社会名人的身份与更为超脱的姿态,倡导国民运动,抨击时弊恶行。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则投入著述与讲学,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新作迭出,方向广博。如诸子学、清学、佛学、文学,此时均做过专门研究,其中尤以史学为大宗。诚如郑振铎先生所言,梁启超后期的学术论著,大致是前期著述时代研究的加深与放大(《梁任公先生》)。而时间余裕,雄心勃勃的梁启超因此又筹划着大型撰著。《清代学术概论》之标为“中国学术史第五种”,《中国历史研究法》之题以“中国文化史稿第一编”,都是拟议中的宏大工程留下的遗迹。与《中国学术史》同年开笔的《中国佛教史》与《国学小史》,则成品更少。由于兴趣广泛且容易转移,梁启超迅速成型的这些计划又每每轻易放弃,使我们今日只能从个别枝节及全书目录来拟想其规模与气魄,因而发出惊叹与感到惋惜。
梁启超这一时期的治学路数,已与传统学者有了很大不同。重视系统性与总体把握,使其研究摆脱了乾嘉考据学派细碎、烦琐的狭小格局,而代之以成型的理论框架结构材料,科学性也得到突出强调。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一文中,梁启超为“科学精神”所作的解说是“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智识的方法”,并据此批评中国旧学界的“笼统”“武断”“虚伪”“因袭”“散失”违背了科学的要求,希望以近代西方的良药医治中国的痼疾,正反映了这种意识的自觉。其论著中的下定义、用推理、作判断,在追求科学化的同时,也使学术研究进一步规范化。梁启超不仅自己做研究讲究方法的运用,如以问题、时代、宗派三种研究法的交叉使用为其学术史撰著的基本法则,而且诲人不倦,喜欢向人传授治学之道。凡此种种,均有益于新型学风的建设与普及。
虽然不再以学干政,而推崇“无所为而为”的治学精神,梁启超其实并非毫无功利的打算,只是不汲汲于现时的效应而已。与倾力从事国民教育的主旨相同,梁启超此时关心的是国民品格的培养,这自然是“新民”课题在现代的延续。不过,也有不同:前时重在批判,此刻重在表彰;前时取法西方,此刻取法传统。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中,梁启超明确将国学研究区分为“文献的学问”与“德性的学问”两类,并且凡语及治学,无不兼及道德修养。即使是以《先秦政治思想史》之名印行的专门论著,他也不忘附加上“中国圣哲之人生观及其政治哲学”的标题,以示别有会心。因而,梁启超此期的学术研究,实可称为“为人生而学问”。他这些与人生不即不离而又具有现代精神、新意浚发、纲目清朗的著述与讲学,便易于在五四以后的知识者尤其是青年学生中引起共鸣,从而名声大振。
概括而言,因政治活动而得名,以学术生涯而葆名,便是梁启超的成功之路。并且,二者相辅相成,去掉任何一方,梁启超的知名度都会大打折扣。
还应当指出的是,梁氏独特的文风,也有利于扩大其社会影响。他在戊戌东渡日本以后创造的“新文体”,“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因此对于当时的读者,“别有一种魔力”(《清代学术概论》)。这种夹杂大量新名词、无所顾忌的采择众多文体(诸如古文、辞赋、骈文、佛典、语录、八股文、翻译文)的字法句式语调融合形成的新型散文,是对传统古体文的极大解放。而其最著名的代表作,即为《少年中国说》。该文首先反复对比老年人与少年人种种对立的性格,并以“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一连九对同类比喻加以强调,最后又气势磅礴地用“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一段韵文结束,其鼓荡人心特别是对热血青年的感召力,便从密集排列的对比句与铿锵有力的节奏中产生。尽管“新文体”带有铺张过度、重叠拖沓、情感刺激过于频繁等明显的毛病,但这些宣传西学、别具一格、热情洋溢的文章,对当时向往新思想、新知识的知识分子,仍具有巨大吸引力。“新文体”之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模仿最多的文体,也是梁启超的文风笼盖社会的明证。
五四文学革命以后,白话文成为社会通行的文体,随时进步的梁启超也抛弃“新文体”,改用这一现代的文字工具。1920年刊出的《欧游心影录》,即是用相当漂亮、流畅的语体文写成。其后大量发表的讲演稿,更是极为生动、传神的口语的摹写。即使在写作学术论文时,梁启超的白话文仍有独特的魅力。它的文字尽管平实,却因与其学术通俗化的学风水乳交融,而能够深入浅出,举重若轻,给人以自由如意的轻松舒畅感。
实在说来,无论问政、述学,也无论治事、行文,统贯梁启超一生的精神追求始终不离乎“开通民智”。报刊政论家心中的读者大众,大学院导师面对的莘莘学子,都与古雅深奥的高头讲章相抵牾。对民众发言的意识既经确立,梁氏前期的介绍西学,倡导政治改良,以及后期的研治国学,促进教育普及,便都在内容与表述的通俗易懂上用力。他为人诟病的肤浅、粗疏,未尝不缘于此;而其广受社会欢迎,知名度居高不下,很大程度也得益于这种努力。
梁启超逝去虽已半个多世纪,他生前探讨的诸多问题,在今日却并未过时,且仍然令人关注。因此,从卷帙浩繁的梁氏著作中撷取有价值的篇章,汇为一编,供现代人阅读、回味,以期引发深入、继续的思考,便是一件很值得去做的事情。本着兼顾文化史意义与文学欣赏趣味的准则,将梁启超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文章择其精要,分类编排,力求窥一斑而知全豹,读其文而知其人,是本文选的努力目标。
入选文章分为十二类,类别顺序及每类文章的排列先后,均大体依照撰写年代以次编定。如以“时论编”居首,“文化编”殿后,便可以反映出梁启超前后期关注重心的转移。梁启超一生笔耕不辍,遗留世间的文字总数约为一千四百万言,可谓著作等身。其生前身后曾出版过多种文集,收集最丰的为中华书局1936年初版的《饮冰室合集》四十册,然而也非全编。此书虽有集大成之长,却也不无瑕疵。以收入的文章而论,有些版本选择不当,校勘不精,并且为求体例的一致,五四以后使用新式标点的文章,也一律改成旧式句读,便是其中最可訾议之处。此次选编,尽量使用较早的版本为底本,与《饮冰室合集》对勘;入选文章,均经标点,原有标点者,只作少量校改,大体保持原样;除个别文章增加了段落划分,基本未加变动。考虑到本书为面向普通读者的通行本,故明显的错字已径行改正,另有拟改之字,以〔〕标出,拟补之字,以( )标出,多衍之字,以〈〉标出。因梁启超行文中征引前人诗文,常凭记忆,故每多讹误,有些收入《合集》的文字已做过校改,有些则仍保持初稿原貌。一般不致误会原意的,不做改正;而出入较大的,则据引用本校出。如《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末二节,未在杂志上刊出,编集时也没能如前八节一般进行校订,错字较多,因此做了集中勘误。每篇文章后面,均注明已知最初的发表时间及出处,个别未审原刊处或完稿后隔年出版者,均标出写作时间。
着手编选时,以为费时无多;深入其中,方觉大非易事。初版本的寻觅、借阅困难,逐字校对,以及由引文而生出的额外校勘,都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也想省点事,降低标准,又觉得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自己。在长夏溽暑之中,总算编完了这几十万字,虽仍有不能令人满意之处,但自问是尽了力了。
1991年8月30日于京西畅春园
此书乃是应我的大学同学沈楚瑾之邀而编,由她作为责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印行了初版,因颇受欢迎,曾经重印。去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再来约请,本人又对原书进行了修订,删去一篇年代不明确者,另补足了《北海谈话记》全文,以其为呈现梁启超晚年思想的重要文献。而最重要的是,此次新增了“家书编”一编。梁家“一门三院士”的佳话早已为人熟知,实则家书中不只蕴含了教子之道,也坦诚地展现了梁启超的情感世界与精神生活,对前列各编所述梁氏的从政与治学,亦从家人的角度做了生动补充。
此次增订,仍对全书文字进行了重新校勘。其间,郭道平与马勤勤两位博士出力最多,在此谨致诚挚谢意。而此项工作花费时间之长完全超出想象,以致答应出版社的交稿日期也一再延展,特别是最初与我联系这一选题的老相识林冠珍竟然等不及拿到书稿,便已于上月退休,这让我非常懊悔。在感谢出版社的包容的同时,我也愿意借此机会,向我尊敬的职业编辑林冠珍致意——她出版的许多好书正站立在我的书架上。
2017年6月6日补记
......(更多)
作者简介
夏晓虹,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先后赴日本、美国、德国、捷克、韩国、英国、马来西亚、以色列、新加坡、法国以及台湾、香港地区从事研究与参加学术会议,并曾在德国海德堡大学(1998)、日本东京大学(1999-2001)、香港岭南大学(2009、2014)客座讲学。主要关注近代中国的文学思潮、女性生活及社会文化。著有《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晚清文人妇女观》《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阅读梁启超》《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晚清白话文与启蒙读物》与《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等。
......(更多)
目录
上卷:
编者前言
《饮冰室文集》自序
时论编
变法通议(节录)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
与严幼陵先生书
《春秋中国夷狄辨》序
知耻学会叙
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
国民十大元气论(节录)
中国积弱溯源论(节录)
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
新民说(节录)
敬告我同业诸君
释革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吾今后所以报国者
外交欤?内政欤?(节录)
杂谈编
傀儡说
动物谈
饮冰室自由书(节录)
少年中国说
呵旁观者文
过渡时代论
说希望
人物编
戊戌政变记(节录)
谭嗣同传
康广仁传
南海康先生传
李鸿章(节录)
(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
三十自述
石醉六藏江建霞遗墨
亡友夏穗卿先生
南海先生七十寿言
游历编
汗漫录(节录)
新大陆游记(节录)
欧游心影录(节录)
宗教编
保教非所以尊孔论
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
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
佛典之翻译(节录)
翻译文学与佛典(节录)
评非宗教同盟
历史编
新史学(节录)
中国历史研究法(节录)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
——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节录)
下卷:
文学编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
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
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节录)
情圣杜甫
美术与生活
屈原研究
稷山论书诗序
书法指导
学术编
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节录)
清代学术概论(节录)
老子哲学(节录)
孔子(节录)
墨子学案(节录)
先秦政治思想史(节录)
戴东原哲学(节录)
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节录)
儒家哲学(节录)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节录)
治学编
西学书目表(节录)
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
东籍月旦(节录)
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
学问之趣味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节录)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节录)
《史记》
《诗经》
指导之方针及选择研究题目之商榷(节录)
人生编
校刻浏阳谭氏《仁学》序
重印郑所南《心史》序
莅同学欢迎会演说辞
“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
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
敬业与乐业
为学与做人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知命与努力
北海谈话记
文化编
复古思潮平议
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
什么是文化?
人生观与科学——对于张丁论战的批评(其一)
非“唯”
家书编
与李蕙仙(1898年11月26日)
与李蕙仙(1900年5月24日)
与梁思顺(1913年1月30-31日)
与梁思顺(1916年2月8日)
与梁思顺(1916年3月20-21日)
与梁思顺(1919年1月13日)
与梁思顺(1922年11月26-29日)
与梁思顺(1923年5月8日)
与梁思成(1923年5月)
与梁思顺(1923年11月5日)
与孩子们(1925年7月10日)
与梁思顺、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庄(1925年10月3日)
与孩子们(1926年10月4日)
与孩子们(1927年2月6-16日)
与孩子们(1927年8月29日)
与孩子们(1927年11月23日-12月5日)
......(更多)
读书文摘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