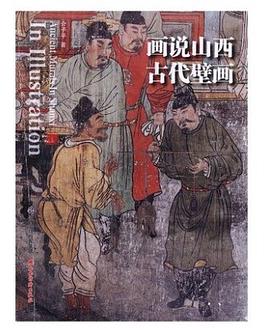内容简介
女兒的憂鬱──朱天心《漫遊者》中的創傷與斷離空間
◎張小虹
朱天心的《漫遊者》,與其說是一本「悼祭之書」,不如說是一本「憂鬱之書」。
「悼祭」(mourning)發生在死亡之後,而「憂鬱」(melancholia)則是在死亡發生之前,便已然開始悼祭。時序錯亂,先於死亡的悼祭,便是憂鬱最初亦最終的徵候。
愛別離苦,女兒的憂鬱就在不甘心「人死了就是死了,不會再有什麼」,女兒的憂鬱是執意要大哉問,究死生、尋意義,不惜上山下海、碧落黃泉,「我且走到了天涯海角……絲毫感覺不出父親可能的去蹤」。
於是憂鬱的女兒將死亡在真正發生之前先孤立出來,成為哲學的命題以沉思,變做文學的想像供端倪。於是憂鬱的女兒在真正的死亡發生之前,先一步踏入語言文字的死亡幽谷,「象徵即對存有物的謀殺」(「The symbol is the murder of the thing.」),進入語言文字的象徵秩序,就是進入另一種死亡。溫厚虔誠的「真實父親」(the real father)在病床上垂危,而語言文字的「象徵父親」(the symbolic father)則早已撒手人寰。
於是憂鬱的女兒在父親過世之前,寫下了〈五月的藍色月亮〉,將死亡比擬做一隻巨大冷酷的貓,咬噬著蜥蜴,「不吞掉,也不鬆口」。文中輾轉反覆的是死亡之後遊魂的去向,「假想自己是隻擅飛的海冬青,展翼於萬呎高空的上升氣流中,任憑海洋、沙漠、落日緩緩靜靜從你爪縫下飄移而去……」。若死亡之後靈魂出竅、離開肉體,那天南地北究竟何去何從,於是揣想出核戰爆發的末日,沒有了飛機輪船,「你得全憑自己的肉身雙腿、執念的往日出處走去。那時候,不再有東方、西方,你得學習以日出日落或那朔風吹起處辨認方向」。
寫在父親過世之前的〈五月的藍色月亮〉,是在死亡發生之前溫柔預演死亡發生之後的景況,擔心害怕如果逝者有靈魂,靈魂如何在畫亂了地圖、不再有東方西方的時空短路中,辨認摸索回家的方向。朱天心曾溫柔地自我解懷道:「父親是替我探路去了,他知道我怕黑、怕鬼、怕病痛、怕死,他常笑我『惡人沒膽』」。而同樣溫柔的是女兒在父親臨終之前,就先用文字替他探路去了,擔心害怕山遙路遠、魂兮歸來。
而寫在父親過世之後的〈出航〉,則依舊念茲在茲遊魂的何去何從,「你無可避免的以你所處的時空想像,想像他正以某種候鳥翱翔的速度,展翼於黑水洋之上」。死亡臨終之時,便是遊魂出航之日,有如「搭乘木柵捷運穿越福州公墓山腹的隧道」,趕黎明前去投胎轉世,棄落一地的喜怒哀樂七情六慾,「情感,像嘩鎯鎯響著好重好重,重得足以拴住一艘大郵輪不使出航的鐵鎖鍊,此時,那鎖鍊被魔法點過似的,已然不見了」。
但〈出航〉比〈五月的藍色月亮〉更憂鬱,更倚重語言文字的象徵,更全然揣想著「自己」而非親人的死亡。逝者已往,無感無知,生者唯有把逝者化入體內,以自己的喜怒哀樂七情六慾去感知,讓生者即逝者,女兒即父親。於是死亡有如往復衝動(repetition compulsion),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搬演,死亡成為「正午太陽一樣,無法直視」的創傷,「無法答話,無法聽見,無法視物」,死亡開啟了象徵秩序與想像秩序之外的「斷離空間」(traumatic space)。
一切只因為憂鬱的女兒望著父親的骨灰盒,「並不覺得父親在那裡」;一切只因為憂鬱的女兒氣急敗壞「你簡直不知道要去哪裡尋他,天國?涅槃?某星座?某次元?某大神腳前?某大氣大化?某「偉大的神秘」中?……」。所以她窮究古今中外,以知識、哲學、秘教、旅行地圖上下求索,那裡去了?那裡去了?用語言文字層層纏繞空無一物的死亡。然而「道」阻且長,語言文字終究緣木求魚,死亡的「斷離空間」非常道、非常名、不可言、無可說。「真實(the real)無法被再現,只可被重複」。《漫遊者》之所以震動人心,正在於無法知曉「斷離空間」為何(what)的當下,讓我們窺探「斷離空間」如何(how)以往復衝動的方式,化象徵為徵候,驅使創作者一而再再而三地以想像演練死亡,以書寫創造死亡。
逝去的父親,「他的頭,像被斬斷似的重重垂在胸前」,憂鬱的女兒,「覺得自己像斷線風箏,可以無罣礙的四下亂跑」,而更大更初的斬斷與裂變,則發生在識得人言人語之後,徹底失落、無法回返「六歲前不被任何知識、神話所干擾吸引的不識字狀態」。於是憂鬱的女兒以人言人語在〈銀河鐵道〉裡逐遊牧之騁,疊合台灣地理與歐亞大陸,穿梭歷史與通俗文化,揣想一條「又孤單又歪七扭八又歧路橫生」的朝聖路,以空間轉換的異國之境「聽不懂周遭人們說什麼,看不懂他們的文字」,來創造另一個時間之流上永不得復返的「不識字狀態」。
但死亡會不會就是另一個回返「不識字狀態」的異國之旅呢?還是〈遠方的雷聲〉裡元宵夜燈籠節那晚突如其來的停電呢?
因為那時遠遠的天際傳來雷聲,庭院內兩年後才會種活的玫瑰和應該是小牛家的葡萄藤氣息一股湧入屋裡,你們趕忙放手顧自家的燈籠罐頭,屋頂地上四壁劇烈的搖晃著人影火光,是父親拉熄了電開關嗎?因為客廳正中懸吊的燈泡突然熄了,屋子黑了,記憶,視網膜上的光點,戛然而止。
「停電了。」有人說。
遠方的雷聲,似遠若近,在記憶的時序跳接裡,玫瑰與葡萄藤的氣息瀰漫一切地,人影幢幢中記憶的光點瞬時熄滅。沒有了光、沒有了影像、亦復沒有了語言文字,黝黑如夜的斷離空間,讓死亡成為傷口,永世無法癒合。
《漫遊者》便是這樣以生者化為逝者的異國他鄉之旅,《漫遊者》便是這樣在語言文字的死亡幽谷裡焦急顧盼,穿不透「斷離空間」的阻隔,回不去「不識字狀態」的混沌。但《漫遊者》的慧黠敏感處仍是朱天心,博學多聞處仍是朱天心,就連忿忿難平處亦是朱天心,雖有《古都》的影子,卻更在真實/想像、夢/醒、遠/近、小說敘事/散文抒情的邊界裡摩搓,在視覺、嗅覺、觸覺的交纏官能裡失魂,卻有更多因死亡引爆的失落與偏執,鍥而不捨一篇接著一篇地論死亡,但所有堆砌舖展的意象與文字,在「說盡」一切能說的之後,就益發讓死亡的「斷離空間」顯得如此道阻且長。
死亡是什麼?花梨木的氣味還是雀榕的澀烈?「彷彿酒醉後坐在微風天的風帆下,醺醺然,那荷花,好香」。
......(更多)
作者简介
......(更多)
目录
......(更多)
读书文摘
我挑战他的一直会在那里,以致一直以为他在盛年而自己十五六岁,永远永远。
本雅明说:“小说家则是封闭在孤立的境地之中,小说形成于孤独个人的内心深处,而这个单独的个人,不再知道如何对其所最执着之事物做出适合的判断,其自身已无人给予劝告,更不知如何劝告他人。写小说是要以尽可能的方法,写出生命中无可比拟的事物……”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