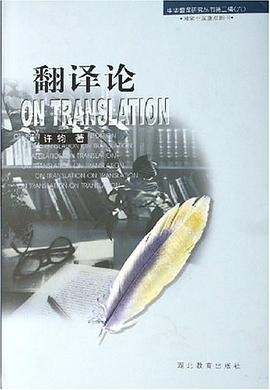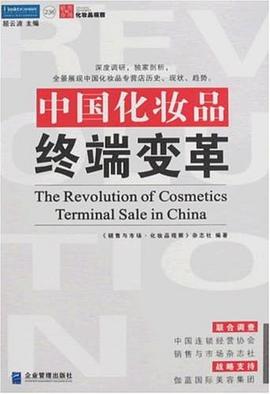内容简介
“尴尬”大都带有两种含义:它首先意味着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其次意味着一种进退两难的神态。前者是内隐的,只有当事者本人意识到;后者是外露的,可以被他人发现和留意。译者的尴尬也不外乎如此,它或隐或露地包含在译者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中。
译者的尴尬完全是由译者的身份认同问题所引发的。当翻译界还主张译者是一个伺时原作者的仆人时,甚至信奉一仆(译者)二主(作者、读者)的观点时,译者的身份是明确的,因此也无尴尬可言。“尴尬”产生在对这样一个理论问题的思考和讨论中:作为译者,我们对原作者的思想究竟应当抱忠实的态度,还是应当持背叛的立场。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早些年里是无须长思的,甚至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但近年来忠实论者受到的质疑甚多,风气一反以往。或许只是由于时代变了,因而突显的问题层面有所不同而已。但是,许多在我看来属于忠实论阵营的翻译实践者和翻译理论家,的确都或多或少在理论上认同并转向背叛论。这是我近年来常常感受到的一个事实,也是我在读完许钧的大作《翻译论》后又一次感受到的事实。[①]
许钧的《翻译论》相当系统周全,没有长年大量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的积累,这样一部论著是拿不出来的。他的翻译论具体说来有翻译本质论、翻译过程论、翻译意义论、翻译因素论、翻译矛盾论、翻译主体论、翻译价值与批评论。但没有见到他提出过翻译类型论。我未做过专门研究,不知是否可以把所有翻译粗略地分为三类:1)技术类、2)文学类、3)思想类。
当然,这种分类是否还有遗漏,这个问题实际上并不重要。因为我在这里的主要意图是想说:如果以技术为主导的翻译与语言学的原理有关,例如与语际转换的规律有关,以文学为主导的翻译与文艺学的原理有关,例如与风格、神韵等等问题有关,那么以思想为主导的翻译就与解释学的原理有关,例如与理解和诠释的可能和限度有关。思想翻译必定包含着诠释的因素,当然首先也就包含理解的因素。而我关注的正是思想翻译。
无疑,思想翻译比其他翻译类型更多地涉及意义问题,首先涉及对作者原意的理解,然后涉及对这个原意的转述。我想翻译界的学者们大都不会否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的成立。再进一步说,如果与意义相对应的是思维,与转述或表述相对应的是语言,那么思想翻译在我看来首先也就是思维和语言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古代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讨论过这个问题,例如作为柏拉图所说的心灵与自身的对话;古代东方的佛教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例如作为意业、语业、身业的关系;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也在讨论,例如作为庄子所说的意与言的关系。到了近代,它更是成为一个关注的焦点,卢梭、赫尔德、洪堡、施莱尔马赫都把这个问题作为自己的思考重点。现代的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也都仍然无法回避。更不用说当代的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心理学和心智哲学,它在这些学科中依然占据着中心问题的位置。
关于思想翻译,前人已经说得很多,有许多可以拿来做参照的。我们这代人还能在此之外提供些什么新的东西呢?我对此把握不大。但我想,如果有,可能就是翻译理论界对译者身份的重新定位。忠实与叛逆,显然与这种对译者身份的重新界定有内在关联。
叛逆论之所以能够在翻译理论界占主导地位,很可能与当下的时代精神过多地偏好解释的权利有关。解释学中的读者中心论,在翻译论这里表现为译者中心论。很难说当代解释学的那几个原初倡导者们会乐于看到这个结果。
即便早个几十年,译者通常也还被要求以化身的方式融在译作之中。译者的主体意识虽然会随译者的自我意识的强弱程度不同而有或显或隐的宣露,但那是不自觉的,例如傅雷的译文风格并不是他本人刻意想要在译文中表露出来的。相反,在翻译一个与自己文笔风格不相容的作品时,译者还更有责任做出压抑自己的努力——当然,最好的方式是干脆不译那些与自己风格迴异的作品。倘若一个演员在演任何一个角色时都只想把他自己演出来,那么这个演员就很难说是出色的。翻译也是如此。W. R. 别林斯基便说过:“如果普希金想翻译歌德,那么我们会期待,在翻译中显现出来的不是他自己,而是歌德。”[②]在年初于中山大学召开的“翻译与解释”的研讨会上,我也曾直言不讳地对许钧说:“我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并不是为了读许钧。”
这些要求应当是不言而喻的,甚至这里的重复都会显得多余。但另一方面又的确可以看到,在主张叛逆论的人中的确有一些像许钧这样的严肃学者,因而叛逆论的提出必定有它的理论基础。
首先需要指出的一点在于,如果有人主张忠实或叛逆,那么首先要弄清,忠实或叛逆是针对什么而言。在思想翻译中,例如在《圣经》翻译中,如果译者的任务像W. 本雅明所说的那样在于传达思想,那么语言表达上的叛逆就是可以容忍的。具体地说,以何种语言符号、表达方式、风格语气来传递同一个思想、转渡同一个意义,这是一个虽然不是无关紧要、但终究还是第二性的问题。与此相反,对思想或意义的叛逆则不被允许,否则译者就是在创作而不是在翻译。这可以算是译者之为译者的身份同一性底线了。
这样的说法当然隐含了一个前提,即:思维和语言并不处在同一个层次上,至少它们是不能相互替代的。这个前提的成立可以依据L. S. 维果茨基的研究成果。他曾借助于格式塔心理学家对类人猿语言与智力以及对发生心理学家对儿童的语言与智力的各项研究成果,得出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结论:“思维与言语具有不同的发生学根源”,“这两个机能沿着不同的路线发展,彼此独立”,而且他尤其指明,“在思维与言语的发展过程中,思维发展有前语言阶段,言语发展有前思维阶段,两者的表现是非常明显的。”
但维果茨基同时还指出,而且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论点:思维机能与言语机能的关系在类人猿那里“不是明确的和不变的”,但在儿童心理的发展中,这两种机能可以汇合,这时,“思维变成了言语的东西,而言语则变成了理性的东西”。[③]正是在这一点上,人类与类人猿这样具有较高智慧的动物关键区别显现出来:惟有在前者那里,思维与言语才相互会合,并且借助于符号而不断得到双方面的提升。可以说,这个过程就是使人类越来越不同于类人猿和其他高级思维动物的东西。
当然,这种会合并不是完全的融合。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确定:存在着“非言语的思维(nonverbal thought)”和“非智力的言语(nonintellectual speech)”。它们各自独立,不参与上述思维和语言的合并,只是间接地受到言语思维过程的影响。[④]
如果我们接受维果茨基的这个研究成果,我们就不必再去考虑一些语言哲学家对思维与语言的同一性问题的思考,例如不再去回答维特根斯坦所提出的小孩子是否“会自发地进行思维,哪怕不学任何一种语言?”的问题。[⑤]也就是说,我们就可以接受思想和语言的非同一性前提。
在这个前提下,当我们谈及翻译的时候,我们可以区分这样两个基本的含义:
第一个含义在于:思维或思想向语言的转渡“转渡”为语言。Translate或übersetzen首先是指将一个从思想转渡到语言,亦即将某些意会的东西转变为言传的东西。这个过程是由原作者本人完成的。这也是原作者能够成为原作者的基本条件。因此,海德格尔会说:“我们始终也在将我们自己的语言、母语转渡到(übersetzen)它自己的语词之中。言说(Sprechen)与言谈(Reden)自身就是转渡……在每一个对话和自身对话中都贯穿着一个原初的转渡……这种转渡(übersetzen)可以在语言表述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发生。”[⑥]
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实际上的复杂性却并不逊于译者所要完成的转渡。因为从思维向语言的转渡原则上包含着两个层面或两个阶段:其一,从思维活动向内部语言的“转渡”,其二,从内部语言向外部语言的“转渡”。
从上面的引文来看,海德格尔趋向于把思想与内部的言说或言谈等同起来。这意味着他在此问题上更多地处在施莱尔马赫而非胡塞尔的影响圈中。胡塞尔曾把意识活动与内心独白和外部传诉明确地区分开来。可以说,胡塞尔的看法更接近于维果茨基的研究成果。在维果茨基那里,这个从思维到语言的转渡还可以进一步分为四个方面:1)动机(情绪、欲望);2)思维;3)内部语言;4)外部语言。它们可以说是勾连心理学和语言学的四环纽带。我们在下面为简单起见只将它们划分为两个环节:内部语言和外部语言。
尤契夫所说的“语言一旦发声就是谎言”,就意味着在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转渡之前,在同一主体内部,思维(内部语言)向语言(外部语言)的转渡已经成为问题。通常所说的“辞不达意”,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表达。
现在来看海德格尔的翻译观,它在总体上仍然是有效的。翻译对于他来说不是重构,而是转渡,即转渡到原初被陈说的东西那里。[⑦]这里含有多重的意思:首先是从思想转渡到内部语言,然后是从内部语言转渡到外部语言——这是作者的任务;然后从外部语言转渡到另一种外部语言——这是译者的任务。
在这里已经提到了思想翻译的第二个基本含义:思想的转渡必须借助至少两种外部语言。这个含义是不言自明的。它也是最一般意义上的翻译的词义,即:将一种外部语言转换为另一种外部语言。但如果我们同时顾及到上述两个含义,那么在翻译中,我们就至少面临双重的转渡问题。事实上,如果从一种外部语言向另一种外部语言的翻译的可能性需要证明,那么从思维向语言(粗略地说:从内部语言到外部语言)的转渡的可能性也需要证明。L. 莱纳斯曾说,“两种不同的语言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可以说,每一个真正的翻译都必须首先将思想剥离开陌生的语词,然后用本己的语词来重新妆扮它。”[⑧]在这里,语言被等同于思想和语词的结合体,而通常意义上的语言则被看作是语词。我们通常所说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针对这个“剥离”和“重新妆扮”的过程而言。
需要说明的是,在一般翻译中,上面所说的第一个含义往往被忽略。这主要是因为,这个从思想到外部语言的转渡过程,在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翻译的过程中被设定为是已经完成的。我们通常不会怀疑,原作者已经通过他自己的语言而将他的思想表达了出来。
一旦这一点受到怀疑,译者的叛逆趋向就会产生。这时我们谈论的“背叛”,不是对原作者思想的背叛,而是对他的语言表达的背叛。如果译者相信,原作者的语言遮蔽了他所想表达的思想,那么译者对原作者语词、语句、乃至风格的叛逆都是合法的。但这个合法性程度最终还是有限的,它取决于译者的信念强度,这个信念是指:他是否通过原作者的语言,比原作者更好地理解了借助这个语言所表达的思想。
这里涉及到了解释学的核心问题。一般说来,解释学否认一个可为所有人达及的客观意义的存在。它认为意义始终处在与意义领会者的互动之中。但解释学并不否认原意的存在,否则我们根本无法谈论意义的转渡。解释学所说的理解意义,相当于对一个思想的再构,这种再构当然不是原创,但也不可能是复制。R. 斯贝曼说:“再构意味着,将一个思想再思考一次,但要思考得更好。根据艺术的规则真正地思考某些在开端上只是模糊地被揣测到的、仅只‘直觉地’被把握到东西。只有能够如此被再构的东西才能被看作是一个真实地被思考的东西。”[⑨]
就此而论,当一个译者去再构原作者的思想时,他有可能比原作者更好地(例如更为圆融地)思考其思想,并且比原作者更好地(例如更为通达地)表达其思想。
可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译者也很难赋予自己总体叛逆的权利。具体地说,译者可以具有对原作语言表述上的某些叛逆权利,但并不具有对原作思想理解上的叛逆权利。如果叛逆论者们承认这一点,那么我们之间的争论便可以休矣。若否,则我还要继续说两句。
我们的确可以承认,价值判断、传统成见预先包含在各种翻译和研究的观念中,不仅人文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也是如此,但这样是否可以得出:追求客观性对于科学家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呢?
对文本的诠释与对真相的认识,道理是一样的。眼下学界对解释学原则的理解过度宣扬了“原意”不在的(严格地说,不“客观地”存在的)方面,却没有说明,“原意”的存在恰恰是各种诠释得以成立的前提。失去了“原意”,或者说,失去了对“原意”存在的信念,各种诠释之间的可比性也就不存在,诠释也就不再是诠释,而变为原创。以绘画为例,我们可以说,一个赝品比一个原作画得更好。但如果根本不存在原作,那么那个被认为是摹仿的作品也就失去作为“赝品”存在的权利。而译作的本质中便包含着“赝品”的成分。在这个意义上,译者与赝品作者一样,是不自由的。
那么译者有没有自己的自由呢?当然有,他可以自由地选择作者、语言、论题、理念、时代、作品、形式、风格等等。但他不能自由地诠释。诠释的主观性并不等于诠释的随意性。这在译者这里就意味着,他必须尽可能地贴近原意,无论他是否能够达到它。这里所说的是我们在翻译中的努力取向:我们必须朝向原意的一极,而不是朝向随意的一极。
译者是否可以比原作者更好地理解原作者本人,这个问题往往取决于译者的主体意识的强弱。我在这点上始终持谨慎的态度。陈修斋先生曾说,“译者切不可以为自己什么都懂”,表达的也是这个态度。在我看来,译者的诠释权利很小,通常只是在原意模糊的情况下才出现。但即便是在这里,我们仍然还有用模糊来应对模糊的可能,在模糊的语言中选择一个比较接近原有模糊含义的翻译。只有当这种可能完全不存在时,举例来说,当我们不知“Bruder”指的究竟是“哥”还是“弟”时,而我们又必须按汉语的习惯来告诉读者是“哥”还是“弟”时;即是说,只有当我们不得不放弃含糊,做出明确的抉择时,我们才有权利做出诠释。
根据上面的划分,今天我们可以在思想翻译的范围内对翻译的理想“信达雅”做如下的阐释:
信:思想的再构。对原作中所要表达的思想的尽可能如实把握。如前所述,它可以说是某种意义的再构,即:将一个思想再思考一次,但思考得更好。
达:语言的重述。用自己的语言尽可能如实地、甚至更通达地表达原作的意义,也就是译者所把握到的原作的思想。
雅:风格的复制。不是风格的修饰,而是尽可能如实地复制原有的风格,无论它本来是雅是俗,是晦是明。
最后再回到许钧的《翻译论》上来。许钧既是《翻译论》的作者,也是昆德拉代表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译者。报载昆德拉在授权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其作品时,要求只有一个,就是“忠实原著”。但译者许钧在他的《翻译论》中则把意大利的俗语“翻译就是叛逆(Traduttore, traditore)”视作一个“朴素的真理”,坦然地予以接受,并且提出翻译中的“意义再生”的主张。[⑩]这里似乎潜含着一场作者和译者间的实际交锋。
然而从媒体的介绍来看,许钧又自认是一个忠实论者,接近原著是他的翻译原则。他在韩少功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与自己翻译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之间划出了一条界线:前者“充满作家个人风格”的作品,后者可以说“更接近原著”的译者作品。如此一来,昆德拉和许钧的交锋反倒像是许钧自己的实践与自己的理论之间的交锋了。
我们是否可以说:实践中的忠实论者,理论上的叛逆论者——这是许钧的尴尬,也是今天诸多译者的尴尬?
本文的意图不仅在于指出这种尴尬,而且还想为从理论上解释和解决这个尴尬提供一个尝试。
2004年6月2日于广州
--------------------------------------------------------------------------------
[①]许钧,《翻译论》,武汉,2003年。许钧在这里很坚定地把“忠实论”描述为“一种天真而理想化色彩浓重的翻译观”(第315页)。
[②]转引自:K. Dedecius, Vom Übersetzen, Frankfurt a.M. 1986, S. 112.
[③]参见维果茨基,《思维与语言》,李维译,杭州,1997年,第46、49页。
[④]维果茨基,《思维与语言》,第54页。
[⑤]参见L. Wittgenstein, Philosophische Bemerkungen, in: Werkausgabe Band 2, Frankfurt a.M. 1981, S. 53 f.
[⑥]M. Heidegger, Parmenides, GA Bd. 54, S. 17 f.
[⑦]R. Spaemann, "Zur Einführung, Philosophiegeschichte nach Martin Heidegger", in: Th. Buchheim (Hrsg.), Destruktion und Übersetzung, Weinheim 1989, S. 5.
[⑧]转引自:K. Dedecius, Vom Übersetzen, Frankfurt a.M. 1986, S. 110.
[⑨]R. Spaemann: "Zur Einführung. Philosophiegeschichte nach Martin Heidegger", in: a.a.O., S. 4 f.
[⑩]参见许钧,《翻译论》,第三章、第六节和第六章、第二节。
......(更多)
作者简介
许钧 现任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讲座教授、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上海大学顾问教授,曾任南京大学教学委员会副主任、现兼任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法语分委员会副主任,国际翻译家联盟科学文献委员会委员,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并担任 META、BABEL、《外语教学与研究》、 《中国翻译》、《外国语》、《译林》、《外国文学》、《南京大学学报》等国内外10余种重要学术刊物的编委或通讯编委。已发表法语语言文学与翻译研究论文250余篇,著作7部,翻译出版法国文学与社科名著30 余部,其译著《追忆似水年华》(卷四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诉讼笔录》及著作《文学翻译批评研究》、《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与接受》、《翻译学概论》等作品,先后十余次获国家或省级优秀成果奖。1999年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兰西金质教育勋章, 2008年和2010年两度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发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称号,2011年获宝钢教育基金会优秀教师特等奖。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