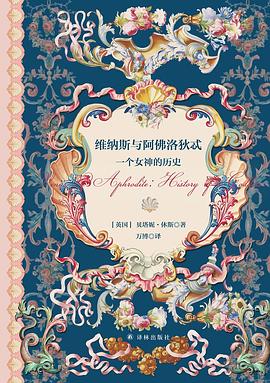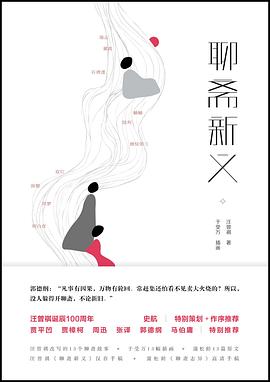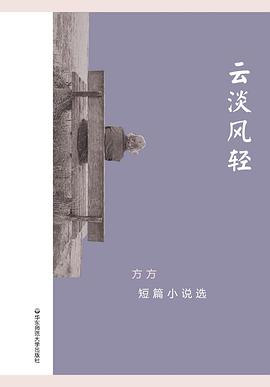内容简介
龍應台的文字,「橫眉冷對千夫指」時,寒氣逼人,如刀光劍影;「俯首甘為孺子牛」時,卻溫柔婉轉彷彿微風吹過麥田。從純真喜悅的《孩子你慢慢來》到坦率得近乎「痛楚」的《親愛的安德烈》,龍應台的寫作境界逐漸轉往人生的深沉。
《目送》的六十八篇散文,寫父親的逝、母親的老、兒子的離、朋友的牽掛、兄弟的攜手共行,寫失敗和脆弱、失落和放手,寫纏綿不捨和絕然的虛無。她寫盡了幽微,如燭光冷照山壁。
這是一本生死筆記,深邃,憂傷,美麗。
......(更多)
作者简介
一九五二年出生於高雄縣大寮鄉,一九七四年畢業於台南成功大學外文系,後獲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英文博士學位,曾任教於美國、台灣、德國多所大學。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三年春為首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現任教於香港大學及台灣清華大學。著有《野火集》、《銀色仙人掌》、《百年思索》、《我的不安》、《孩子你慢慢來》等十多部作品。
龍應台近年常駐三個地址:香港沙灣徑二十五號濱於海、台北仰德大道白雲山莊藏於山,金華街月涵堂隱於市。寫作教書兼成立基金推動全球意識之餘,最流連愛做之事,就是懷相機走山走水走大街小巷,上一個人的攝影課。
......(更多)
目录
......(更多)
读书文摘
我们都知道了:妈妈要回的“家”,不是任何一个有邮递区号、邮差找得到的家,她要回的“家”,不是空间,而是一段时光,在那个时光的笼罩里,年幼的孩子正在追逐笑闹、厨房里正传来煎鱼的嗞嗞香气、丈夫正从她身后捂着她的双眼要她猜是谁、门外有人高喊“限时挂号拿印章来”…… 妈妈是那个搭了“时光机器”来到这里但是再也找不到回程车的旅人。
幸福就是,生活中不必时时恐惧。幸福就是,寻常的人儿依旧。幸福就是,早上挥手说“再见”的人,晚上又平平常常地回来了,书包丢在同一个角落,臭球鞋塞在同一张椅下。
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去看父母的背影,更多的时候是我们承受爱我们的人追逐的目光,承受他们不舍的,他们不放心的,满眼的目送。但我们从小到大只管着一心离开,从未回头张望过。
醒来,方知是梦,天色幽幽,怅然不已。
纵有千般不舍,终有离别时。
斜坡上的杂花野草,谁说不是一草一千秋,一花一世界呢?
家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段时光。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一个人走路,才是你和风景之间的单独私会。
你我还会这样相聚吗?我们会不会,像风中转蓬一样,各自滚向渺茫,相忘于人生的荒漠。
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zhi,只能一个人走。
幸福就是,早上挥手说“再见”的人,晚上又平平常常地回来了,书包丢在同一个角落,臭球鞋塞在同一张椅下。
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幸福就是:生活中不必时时恐惧。
不需要对生活太用力,心会带着我们去该去的地方
沙上有印,风中有音,光中有影。
你能想象比‘被物质撑得过饱后的漠然’更贫乏的存在状态吗?
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行走,身上没有一个包袱,手里没有一张地图。
眼睛熟悉了黑暗,张开眼,看见的还是黑暗。
怎么就知道,你活得比我长呢?时间才是最后的法官。
太疼的伤口,你不敢去触碰;太深的忧伤,你不敢去安慰;太残酷的残酷,有时候,你不敢去注视。
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
不是渐行渐远,而是有一天终要重逢;你的名字,清楚地留在世纪的史记里。
理想主义者要有品格,才能不被权力腐化;理想主义者要有能力,才能将理想转化为实践。
因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往而不在枷锁中,所以人们渴望着远方。
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
外面的世界固然荒凉,但是家可以更寒冷。
寂寞的感觉,像沙尘暴的漫天黑尘,以鬼魅的速度,细微地渗透地包围过来。
奢侈,到底是一种被物质撑得过饱的漠视,还是把一切都看的都理所当然的无聊?
他好像在听一个不可及的梦想,又仿佛在夜行暗路上突然听见熟悉的声音,轻轻呼唤自己的名字,带点不可思议的向往与情怯:是啊,太湖边,柳树下,线装书......
我坐在风暴中心,四周却一片寂静,这是寂寞的感觉,像沙尘暴的漫天黑沙,以鬼魅的速度,细微地渗透地包围过来。
斜坡上的杂化野草,谁说不是一草一千秋,一花一世界呢?
贫穷的记忆,在事过境迁之后,像黑白片一样,可能产生一种烟尘朦胧的美感,转化为辛酸而甜美的回忆。
空荡荡的街,只有我,和那生了我的女人。
我们拼命地学习如何成功冲刺一百米,但是没有人教过我们:你跌倒时,怎么跌得有尊严;你的膝盖破得血肉模糊时,怎么清洗伤口、怎么包扎;你痛得无法忍受时,用什么样的表情去面对别人;你一头栽下时,怎么治疗内心淌血的创痛,怎么获得 心灵深 层的平静;心像玻璃一样碎了一地时,怎么收拾?
母亲,是个最高档的全职、全方位CEO,只是没人给薪水而已。
在暂时里,只有假设性的永久和不敢放心的永恒。
在平凡和现实里,也必有巨大的美的可能吧。
怎么就知道,你活得比我长呢?时间才是最后的法官。
九十三岁的眼睛和四岁,竟是同一双眼睛?灵魂里,还是那看《史记》的孩子,深情而忧郁的青年?
中年人的沧桑中,总有一种无言的伤痛。目送生命的逝去,目送生命的远行,却只能目送,无法挽留。
回忆真的是一道泄洪的闸门,一旦打开,奔腾的水势慢不下来。
金门的美,怎么看都带着点无言的忧伤。一栋一栋颓倒的洋楼,屋顶垮了一半,残破的院落里柚子正满树摇香。如果你踩过破瓦进入客厅,就会看见断壁下压着水渍了的全家福照片,褪色了,苍白了,逝去了。一只野猫悄悄走过墙头,日影西斜。
春节的爆竹在冷过头的冬天有一下没一下的,凉凉的,仿佛浸在水缸里的酸菜。——龙应台 《目送》
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人生就是如此,你以为已经从一个漩涡逃离,其实另外一个漩涡就在你的脚下。用力蹬一脚,就进去了。所以,不需要对生活太用力,心会带着我们去该去的地方。
拜祭,终究也只是生者的一份安宁。
你能想象比‘被物质撑得过饱后的漠然’更贫乏的存在状态吗?
我们这一代人,错错落落走在历史的山路上,前后拉得很长。同龄人推推挤挤走在一块,或相濡以沫,或怒目相视。年长一点的默默走在前头,或迟疑徘徊,或漠然而果决。前后虽隔数里,声气婉转相通,我们是用一条路上的同代人。
他的坐着,其实是奔波,他的热闹,其实是孤独,他,和他的政治对少们,所开的车,没有”R”挡,更缺空挡。
相机,原来不是那么重要,它不过是我心的批注,眼的旁白。
世上六十亿人里,没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可能居大多数。
时光,是停留还是不停留?记忆,是长的还是短的?一条河里的水,是新的还是旧的?每一片繁花似锦,轮回过几次?
人对自然、对生命过度地暴虐、亵渎之后,他究竟还有什么依靠呢?如果勇敢领袖们的心里深埋着仇恨和野心的地雷,敏感的阿拉伯芥又救得了几个我们疼爱的孩子呢?
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
理想主义者往往经不起权力的测试。
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
对于行路的我而言,曾经相信,曾经不相信,今日此刻也仍旧在寻找相信。但是面对时间,你会发现,相信或不相信都不算什么了。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母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修行的路总是孤独的,因为智慧必然来自孤独。
每一个被我“看见”的瞬间刹那,都被我采下,而采下的每一个当时,我都感受到一种“美”的逼迫,因为每一个当时,都稍纵即逝,稍纵,即逝。
如果科学家能把一滴眼泪里所有的成分都复制了,包括水和盐和气味、温度——他所复制的,请问,能不能被称作一滴“眼泪”呢?
“所有其他的人,会经历结婚、生育、工作、退休,人生由淡淡的悲伤和淡淡的幸福组成,在小小的期待、偶尔的兴奋和沉默的失望中度过每一天,然后带着一种想说却又说不来的‘懂’,做最后的转身离开。”
太疼的伤口,你不敢去触碰;太深的忧伤,你不敢去安慰;太残酷的残酷,有时候,你不敢去注视。
要真正的注视,必须一个人走路。一个人走路,才是你和风景之间的单独私会。
我们都知道了,母亲要回的”家“,不是任何一个有邮递区号、邮差找得到的家,她要回的”家“,不是空间,而是一段时光。
凡是出于爱的急切都是可以原谅的。
一个人固然寂寞,两个人孤灯下无言相对却可以更寂寞。
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心中渐渐有一分明白,如月光泻地。
南美洲有一种树,雨树,树冠巨大圆满如罩钟,从树冠一端到另一端可以有三十米之遥。阴天或夜间,细叶合拢,雨,直直自叶隙落下,所以叶冠虽巨大且密,树底的小草,却茵茵然葱绿。兄弟,不是永不交叉的铁轨,倒像同一株雨树上的枝叶,虽 然隔开 三十米,但是同树同根,日开夜合,看同一场雨直直落地,与树雨共老,挺好的。
真正能看懂这世界的,难道竟是那机器,不是你自己的眼睛、你自己的心?
妈妈是那个搭了“时光机器”来到这里但是再也找不到回程车的旅人。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 ? ? ? 寻找有时、放手有时,保持有时、舍弃有时 ? ? ? 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穆有时、言语有时 ? ? ? 喜爱有时、恨恶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 ? ? ? 难的是,你如何辨识寻找和 放手的 时刻,你如何懂得,什么是什么呢?
所有美好的都已美好的过去了,甚至夜夜来吊唁的蝶梦也冷了。是的,至少你还有虚无留存。你说,至少你已懂得什么是什么了。是的,没有一种笑是铁打的,甚至眼泪也不是。
不是渐行渐远,而是有一天终要重逢。
文明和野蛮的中隔线,薄弱,混沌,而且,一扯就会断。
冬夜的街,很黑,犬吠声自远处幽幽传来,听起来像低声呜咽,在解释一个说不清的痛处。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
幸福就是,生活中不必时时恐惧[lizhigushi.com]。幸福就是,寻常的人儿依旧。幸福就是,早上挥手说“再见”的人,晚上又平平常常地回来了,书包丢在同一个角落,臭球鞋塞在同一张椅下。
所谓了解,就是知道对方心灵最深的地方的痛处,痛在哪里。
人在天地之间终究是无所凭依的孤独,你真能面对生老病死,就真的明白,在这世间,没有什么可以附着依托。
才子当然心里冰雪般的透彻: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曾经相信过海枯石烂作为永恒不灭的表征,后来知道,原来海其实很容易枯,石,原来很容易烂。雨水,很可能不再来,沧海,不会再成桑田。原来,自己脚下所踩的地球,很容易被毁灭。海枯石烂的永恒,原来不存在。
我坐在风暴中心,四周却一片死静,这时,寂寞的感觉,像沙尘暴的漫天黑尘,以鬼魅的流动速度,细微地渗透地包围过来。
歌声像一条柔软丝带,伸进黑洞里一点一点诱出深藏的记忆;群众跟着音乐打拍,和着歌曲哼唱,哼唱时陶醉,鼓掌时动容,但没有尖叫跳跃,也没有激情推挤,这,是四五十岁的一代人。
每一个被我“看见”的瞬间刹那,都被我采下,而采下的每一个当时,我都感受到一种“美”的逼迫,因为每一个当时,都稍纵即逝;稍纵,即逝。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时间是一只藏在黑暗中的温柔的手,在你一出神一恍惚之间,物走星移。
有一种寂寞,身边添一个可谈的人,一条知心的狗,或许就可以消减。有一种寂寞,茫茫天地之间余舟一芥的无边无际无着落,人只能各自孤独面对,素颜修行。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