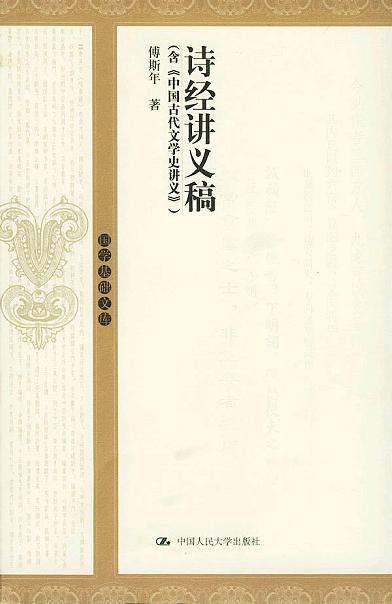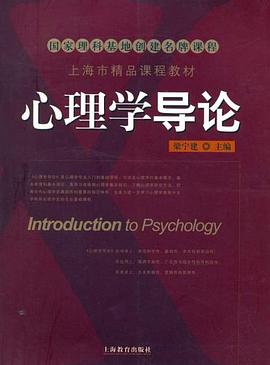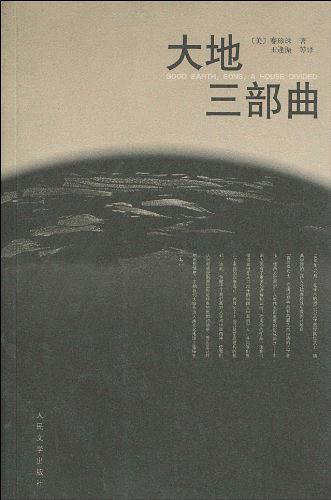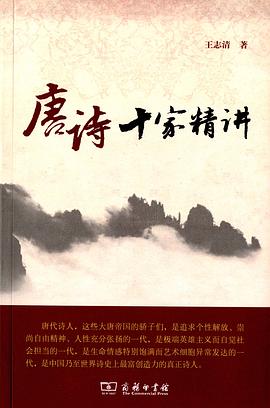内容简介
下列关涉(诗经》之讲义十二篇,大体写就于民国十七年十二月,其《周颂》一篇,十一月所写,论文辞之一节,次年一月所补也。日中无暇,每晚十一时动笔写之,一日之劳,已感倦怠,日之夕矣,乃须抽思,故文辞不遑修饰,思想偶涉枝节。讲义之用本以代言,事既同于谈话,理无取乎断饰,则文言白话参差不齐之语,疏说校订交错无分之章,聊借此意自解而已。其中颇有新义,深愧语焉不详,此实初稿,将随时删定,一年之后,此时面目最好无一存也。此为论经之上卷,所敷陈诸题多为叙录《诗经》而设,中卷将专论语言文字中事,下卷则谈《诗经》旁涉所及之问题,均非今年所能写就。若所写就者,幸同学匡其失正其
误也。
-诗三百篇”自是一代文辞之盛,抑之者以为不过椎轮,扬之者以为超越李杜,皆非其实。文学无所谓进步,成一种有机体之发展则有之。故一诗之美,可以超脱时间,并非后来居上;而一体之成,由少而壮,既壮则老,文学亦不免此形役也。《诗经》之辞,有可以奕年永世者,《诗经》之体,乃不若五言七言之盛,则亦时代为之耳。欣赏之盛,尽随主观,鸠摩罗什有言,嚼饭与人,乃令呕吐。故讲习《诗经》最宜致力者,为文字语言之事,兹编未之及,留待中卷,以此事繁博非短时整理所能得其条贯。若论文辞一节,应人之请强为主观之事作解说,恐去讲章无几,删之亦可也。
《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拟目中三节涉及《诗经》者(第二篇四、五、八),即以此卷代之。此卷所论为叙录《诗经》,文学史中所应述说,理非二事,故不别作。
......(更多)
作者简介
......(更多)
目录
......(更多)
读书文摘
“但是据我看来,他实在比毛公的传,郑君的笺,高出几百倍。就是后人的重要著作,像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陈奂的《毛诗传疏》、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虽然考证算胜场了,见识仍然是固陋的很,原敌不上朱晦庵。”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