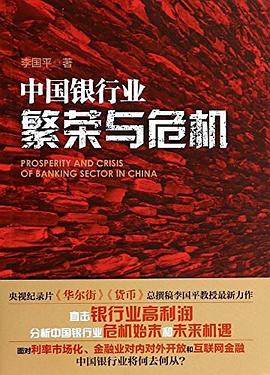内容简介
「每次得知有朋友要出遠門,將去的城鎮倘我曾經玩過,我總是很多事的想寫下兩三頁紙,上面記著我覺得他應該去玩去看去吃的地點,讓他帶著上路。……
「我當然也一直想把京都的好玩地點寫在紙上給朋友。這個念頭已有很多年了。一開始我大約會寫下:◎石土屏小路◎宇治川兩岸。沿著川散步,最富閒情。川北岸的「宇治上神社」與南岸的「平等院」不妨只用來當作散步中某一轉折時的點景可也。◎「綿熊蒲鉾店」的甜不辣,如同在台灣所吃之口味,而更勝。◎「茂庵」。開在吉田山頂的木屋式咖啡館。幾次之後,愈寫愈多,如此愈發不易只是兩三張紙了。最後,索性寫成一本小書算了。
「但我仍然希望它像兩三頁紙那樣的隨便、那樣的輕巧、那樣的簡略,以及,那樣的像寫給熟朋友的、我想怎麼說就怎麼說的自在。不知道容不容易做到。」──〈何以寫此書〉
********************
一九八三年,二十啷噹的他,推開纔溫熱的copywriter文案,站起身來,舉步出發。
從此再也不曾停下。
幾十年了。
他,總是在晃蕩。
在台灣,在日本,在香港。
從理想的下午漫晃到小食的夜宵,
從西湖的曉風殘月浪蕩去紐約的街巷大道。
他,是六○年代波希米亞的孑遺,
是真正嬉皮精神的延續,
更是浸潤晚明風流的古人在今。
這次,他晃蕩到千年的京都。
他說他是門外漢,
略略一望,
卻盡是巷內人不見的風物景。
......(更多)
作者简介
舒國治
七○年代便以少少幾篇作品(如小說〈村人遇難記〉)嶄露頭角。原有意投身電影,終仍返回寫作。一九八三至一九九○,七年浪跡美國;一九九八獲長榮旅行文學獎首獎之〈遙遠的公路〉可算此期間生活與創作的寫照。
一九九○年冬返台長住,自此所寫,好談旅行、談七○年代如〈台北遊藝〉、談小吃如〈粗疏談吃〉、談台北如〈水城台北〉,談搖滾談流浪談走路,題材寬廣,風格自成一家。
著有《理想的下午》《讀金庸偶得》(皆遠流),《台灣重遊》(作者自印),《生活筆記》一九七七年版之〈人名索引〉。
......(更多)
目录
读书文摘
曾经我站在鸭川边,见流水淙淙,何等的清澈凉洌,川上时有飞鸟伫停,准备觅食。川的两岸,有几撮人散座石上,与我一样享受着这空灵却有流畅的无尽延伸野外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