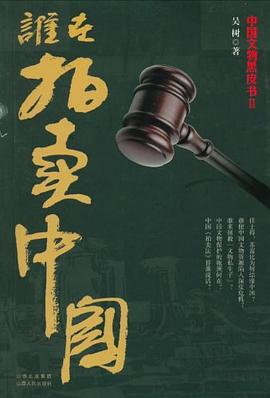内容简介
A.愛德華.紐頓(Alfred Edward Newton)
一八六四年∼一九四○年。美利堅合眾國費城商界人士,卡特電器設備製造公司持有人暨經營者。愉暇以閱讀、藏書自娛。屢次造訪倫敦,多為購置心儀古籍、手稿。
與芭貝特.艾德罕結縭多年,膝下育有子女各一:長女卡洛琳與次男E.史威夫特。一家人適居費城市郊戴爾斯福郡橡樹丘、紐頓本人設計興建之宅舍。
一九一八年,散文集《藏書之樂及其相關逸趣》問世,不但立即暢銷,並成為同類著作之經典。此後他繼續發表許多與藏書、旅遊相關的文章且一一集結出版,皆廣受讀者歡迎。
紐頓生前為葛羅里亞俱樂部的忠實會員,並曾自組「安東尼.特洛羅普學會」。
譯按:以上為某名人錄中所登載的紐頓正式簡介,雖然可大致可從中得知此君中、晚年生平梗概,但我個人覺得這種陳述方式實在太不「紐頓」(newtonian)了,況且全文對於他最精采的早年事蹟未置一詞。我將手邊各種資料重組一次,以更接近紐頓氣質的文句另擬一則:
阿弗烈.愛德華.紐頓,土生土長費城人,幼時一度短居紐澤西。此君雖僅接受過區區數年正規教育,反而提供他自學契機;少年紐頓於中輟學業後自商販學徒起家,酷愛文學之餘困知勉行,亦頗成一番氣象。平生最愛蘭姆、狄更斯、布雷克、特洛羅普、哈代等英國大家,亦心儀約翰生博士、鮑斯威爾當代英倫文藝氣氛,倫敦成為其最鍾愛城市自不迨言,自一八八四年首度造訪,此後頻頻出入,專程前往、隨念轉赴,公幹、私遊兼有之。
紐頓聚書多年頗得成績,偶然為文論述藏書點滴,不意大受歡迎,此後集稿陸續成書,除其中一、二種刁鑽版本論著外,各書皆長年暢銷不輟(直至二十世紀中葉始退熱潮)。生前雖不見遠大抱負(除藏書一事),然興趣、工作皆屢獲貴人襄助,一路步步高昇,直至坐擁藏書萬卷、位居職場龍頭;乃因此自況曰:「鴻福齊天。」藏書、著書之餘,紐頓亦喜好出版,頻頻以自藏珍本印行小冊、複製畫葉分贈親朋好友。所結交者俱為俊彥鴻儒,屢屢不吝出示珍藏,供各界治學研究。於文化之功甚偉。
紐頓乃性情中人,生性風趣健談,為文妙語如珠;以赤誠厚待諸友眾人,其間亦不乏戲謔親暱,友人稱他作「今之匹克威克」。雖履履於文中自曝「敬內」(「懼內」)德性,實則紐頓伉儷感情甚篤,歷次出遊皆出雙入對。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之一九四○年深秋,經過長達一年的癌症摧折,紐頓終不治故去(享年七十有六),引起(大西洋)兩岸書友、讀者不勝唏噓;翌年大戰勃發,藏書之黃金年代就此暫告終結,紐頓生前深愛之老倫敦亦歷盡劫數不復往昔矣。
......(更多)
作者简介
此次收入中文譯本的篇章,分別選自紐頓的五部同類著作:《藏書之樂,及其相關逸趣》(The Amenities of Book-Collecting and Kindred Affections, 1918)、《洋相百出話藏書,兼談藏書家的其他消遣》(A Magnificent Farce and Other Diversions of a Book-Collector, 1921)、《最偉大的書,與其他零篇》(The Greatest Book and Other Papers, 1925)、《蒐書之道》(This Book-Collecting Game, 1928)、以及《蝴蝶頁——文藝隨筆集》(End Papers: Literary Recreations, 1933),恰分為五卷都十九章。挑選的標準稍有參差,但約略以「較符合『藏書』旨趣」與「有特殊的文藝趣味」者為原則(唯一的例外是完全不涉及藏書的〈志願人人有,我的不算多!〉)。當然,未收錄的其他文章亦盡是字字珠璣逗趣、篇篇雋永可讀,惟考量篇幅有限,或其內容與今日此間讀者的距離更大,只有割愛遺珠一途。但我仍將五部書的完整目錄翔實列出(在各卷開頭),並略述該文內容梗概,由讀者們自行一一睹目遐想。
法國鋼古紙書衣,布質精裝封面
Alfred Edward Newton A.愛德華.紐頓(一八六四年~一九四○年)
美利堅合眾國費城商界人士,卡特電器設備製造公司持有人暨經營者。愉暇以閱讀、藏書自娛。屢次造訪倫敦,多為購置心儀古籍、手稿。
與芭貝特.艾德罕結縭多年,膝下育有子女各一:長女卡洛琳與次男E.史威夫特。一家人適居費城市郊戴爾斯福郡橡樹丘、紐頓本人設計興建之宅舍。 一九一八年,散文集《藏書之樂及其相關逸趣》問世,不但立即暢銷,並成為同類著作之經典。此後他繼續發表許多與藏書、旅遊相關的文章且一一集結出版,皆廣受讀者歡迎。
紐頓生前為葛羅里亞俱樂部的忠實會員,並曾自組「安東尼.特洛羅普學會」。
譯按:以上為某名人錄中所登載的紐頓正式簡介,雖然可大致可從中得知此君中、晚年生平梗概,但我個人覺得這種陳述方式實在太不「紐頓」(newtonian)了,況且全文對於他最精采的早年事蹟未置一詞。我將手邊各種資料重組一次,以更接近紐頓氣質的文句另擬一則:
阿弗烈.愛德華.紐頓 土生土長費城人,幼時一度短居紐澤西。此君雖僅接受過區區數年正規教育,反而提供他自學契機;少年紐頓於中輟學業後自商販學徒起家,酷愛文學之餘困知勉行,亦頗成一番氣象。平生最愛蘭姆、狄更斯、布雷克、特洛羅普、哈代等英國大家,亦心儀約翰生博士、鮑斯威爾當代英倫文藝氣氛,倫敦成為其最鍾愛城市自不迨言,自一八八四年首度造訪,此後頻頻出入,專程前往、隨念轉赴,公幹、私遊兼有之。
紐頓聚書多年頗得成績,偶然為文論述藏書點滴,不意大受歡迎,此後集稿陸續成書,除其中一、二種刁鑽版本論著外,各書皆長年暢銷不輟(直至二十世紀中葉始退熱潮)。生前雖不見遠大抱負(除藏書一事),然興趣、工作皆屢獲貴人襄助,一路步步高昇,直至坐擁藏書萬卷、位居職場龍頭;乃因此自況曰:「鴻福齊天。」藏書、著書之餘,紐頓亦喜好出版,頻頻以自藏珍本印行小冊、複製畫葉分贈親朋好友。所結交者俱為俊彥鴻儒,屢屢不吝出示珍藏,供各界治學研究。於文化之功甚偉。
紐頓乃性情中人,生性風趣健談,為文妙語如珠;以赤誠厚待諸友眾人,其間亦不乏戲謔親暱,友人稱他作「今之匹克威克」。雖履履於文中自曝「敬內」(「懼內」)德性,實則紐頓伉儷感情甚篤,歷次出遊皆出雙入對。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之一九四○年深秋,經過長達一年的癌症摧折,紐頓終不治故去(享年七十有六),引起(大西洋)兩岸書友、讀者不勝唏噓;翌年大戰勃發,藏書之黃金年代就此暫告終結,紐頓生前深愛之老倫敦亦歷盡劫數不復往昔矣。
Alfred Edward Newton A.愛德華.紐頓(一八六四年~一九四○年)
美利堅合眾國費城商界人士,卡特電器設備製造公司持有人暨經營者。愉暇以閱讀、藏書自娛。屢次造訪倫敦,多為購置心儀古籍、手稿。
與芭貝特.艾德罕結縭多年,膝下育有子女各一:長女卡洛琳與次男E.史威夫特。一家人適居費城市郊戴爾斯福郡橡樹丘、紐頓本人設計興建之宅舍。 一九一八年,散文集《藏書之樂及其相關逸趣》問世,不但立即暢銷,並成為同類著作之經典。此後他繼續發表許多與藏書、旅遊相關的文章且一一集結出版,皆廣受讀者歡迎。
紐頓生前為葛羅里亞俱樂部的忠實會員,並曾自組「安東尼.特洛羅普學會」。
譯按:以上為某名人錄中所登載的紐頓正式簡介,雖然可大致可從中得知此君中、晚年生平梗概,但我個人覺得這種陳述方式實在太不「紐頓」(newtonian)了,況且全文對於他最精采的早年事蹟未置一詞。我將手邊各種資料重組一次,以更接近紐頓氣質的文句另擬一則:
阿弗烈.愛德華.紐頓 土生土長費城人,幼時一度短居紐澤西。此君雖僅接受過區區數年正規教育,反而提供他自學契機;少年紐頓於中輟學業後自商販學徒起家,酷愛文學之餘困知勉行,亦頗成一番氣象。平生最愛蘭姆、狄更斯、布雷克、特洛羅普、哈代等英國大家,亦心儀約翰生博士、鮑斯威爾當代英倫文藝氣氛,倫敦成為其最鍾愛城市自不迨言,自一八八四年首度造訪,此後頻頻出入,專程前往、隨念轉赴,公幹、私遊兼有之。
紐頓聚書多年頗得成績,偶然為文論述藏書點滴,不意大受歡迎,此後集稿陸續成書,除其中一、二種刁鑽版本論著外,各書皆長年暢銷不輟(直至二十世紀中葉始退熱潮)。生前雖不見遠大抱負(除藏書一事),然興趣、工作皆屢獲貴人襄助,一路步步高昇,直至坐擁藏書萬卷、位居職場龍頭;乃因此自況曰:「鴻福齊天。」藏書、著書之餘,紐頓亦喜好出版,頻頻以自藏珍本印行小冊、複製畫葉分贈親朋好友。所結交者俱為俊彥鴻儒,屢屢不吝出示珍藏,供各界治學研究。於文化之功甚偉。
紐頓乃性情中人,生性風趣健談,為文妙語如珠;以赤誠厚待諸友眾人,其間亦不乏戲謔親暱,友人稱他作「今之匹克威克」。雖履履於文中自曝「敬內」(「懼內」)德性,實則紐頓伉儷感情甚篤,歷次出遊皆出雙入對。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之一九四○年深秋,經過長達一年的癌症摧折,紐頓終不治故去(享年七十有六),引起(大西洋)兩岸書友、讀者不勝唏噓;翌年大戰勃發,藏書之黃金年代就此暫告終結,紐頓生前深愛之老倫敦亦歷盡劫數不復往昔矣。
藏書誠有樂,禍害尤其多
一年多前,我初試拙筆斗膽譯出《查令十字路84號》,那部小書在愛書人的小圈子裡似乎引起小小的迴響,出版公司的編輯每隔一陣子碰到我總不忘好心賜告:銷售數字越來越可觀,又送廠幾刷云云(當然,絲毫不敢高攀《牙套》、《靚湯》或《教你詐》、《蛋白女》之屬);所有結果都令我大感意外:一來,我乃區區一介門外漢,竟然也能(或,也敢)涉足翻譯;再者,在這個沒有氣質的地方,居然還有不少人甘願買書來讀(或許真該感謝咱們的公共圖書館一向效能不彰)。套句A.愛德華.紐頓得知他的書居然能賣到接二連三再版時脫口而出的話:「Bewildering!」
該書出版不久後,我讀到楊照的文章1,他在該文結尾登高呼籲眾愛書同志放心大膽效法他「理直氣壯」起來:
很不幸的,在台灣,太少人這樣面對書,少到他們都感受到自己的稀奇,變得膽怯退縮,無法理直氣壯。膽怯退縮到根本不相信這種書,在台灣會有市場。他們羨慕海蓮.漢芙近乎狂傲的理直氣壯,因為太羨慕了,所以不敢相信可以把如此這般理直氣壯帶進台灣來。
《查令十字路84號》終於有了台灣版中譯本,「愛書人」們可以開始試著更理直氣壯了些嗎?
善哉斯言!在下正是芸芸眾「膽怯退縮的讀者」之一,也是當初不敢如此這般「理直氣壯」看好那部小書銷路的傢伙。我從翻找父親的書架啟蒙;後來學會在書店打書釘,遇到不讓白看的店家便轉戰他處或萬不得已自掏腰包;窮途末路之餘再從國外郵購尚無中文譯本的書(有時候也不得不重買被譯壞了的原書),一路走來始終不曾理直氣壯過。雖屢屢動念,想推薦幾部我心目中的好書給出版界的朋友進行中譯以饗無數國人(或其中極少數的愛書同胞);但是顧慮各出版社普遍營運慘澹,加上每每在書店被所謂「暢銷排行榜」的惡形惡狀嚇得六神無主,我便自反而縮,回頭悶讀自己中意的書作罷。漢芙想必鼓舞了一批原本「膽怯退縮」的讀者,楊照更適時揭竿起義(再次感謝因為讀了唐諾和楊照的文章而逛進查令十字路的讀友);楊照還在文章中扯出一部問世於二十世紀初葉的名著《藏書之樂,及其相關逸趣》。我猜,八成是某位出版界的高人讀過那篇文章之後,果真理直氣壯起來了;而他們響應楊照的具體作法居然是:再度發難、嘗試另一部後市不怎麼看好的書(真希望事後能證明我又錯了)。
這裡先小小地糾正楊照,那部書其實早在十年前就有了中文譯本:由趙台安、趙振堯兩位先生合譯的《聚書的樂趣》,一九九二年收在北京三聯書店「文化生活譯叢」之下,與李約瑟、吉朋、勞倫斯、葛林等名家並列。前一陣子,我收到朋友轉寄來的電子郵件,其中夾帶一篇〈窮愛書人之歌〉,乍讀之下我覺得有點兒眼熟,並循線在某網站看到幾位愛書網友(這個詞兒怎麼唸怎麼彆扭)正在四處流傳這首詩,我翻找出一直不堪卒讀的三聯譯本,不由得教我心急如焚。
蓋那首詩正出自趙譯本,該版本舛誤、闕漏頗多。天可憐見,吾島同胞若壓根從未聽過、從沒讀過那部書也就罷了,但是錯陋譯文鳩占鵲巢可萬萬不能坐視。恰好稍早出版社來電囑我中譯這部書,由於我若干年前即讀過紐頓的幾部著作,深知此項任務艱辛可期——二十世紀初莊諧並濟的文體、古籍版本專業術語之刁鑽、英語文藝傳統之堂奧、風土國情的差別異變……在在都是坎坷前途,更甭提我個人絲毫不具備翻譯或文學專業的資歷、造詣。前幾天我上網查資料,看到有人在某留言板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該匿名留言者自稱「曾與畢業於T大考古系的《查令十字路84號》譯者陳建銘在E書店共事……」為了避免以訛傳訛,我鄭重在此坦白招供:敝人非但不是她(或他?)所指那所T大的畢業生,連另一所T大短短四年的一半也沒本事唸完,勉強湊足一年半的大學生涯也多半沒待在課堂裡;漢芙寫過的一句話可資自況:「我非但一丁點兒學問都沒有,連大學也沒上過哩!」2但回頭思及紐頓原書已絕版多時,雖然在國外的舊書店並不難找,若非首版附原書衣的本子,價格也還算便宜,但畢竟不便苛求每位有心讀者都去找原書來讀(雖然我認為那才是上上策);另一個更迫切的危機則來自極有可能會被傳布的北京三聯版(據悉最近大量重刷),島內有不少愛書人「不幸」讀過那個本子,因一時失察不慎引用,其中若干誤譯因而大剌剌地傳染了某些國人文章。我心一橫,再度不自量力、硬著頭皮攬下譯務。
若干年前,我的確曾有幸在一家十分聞名、來客甚多的大書店裡頭一方門可羅雀、冷冷清清的小角落忝任古書部門負責人(記憶所及,除了「成天窩在店內看書」之外,我好像從沒負過什麼責)。囿於時空條件,當時所能經營的品目自然與紐頓在文章中所提及的各種珍稀善本有著雲泥般的差野;既無緣經眼,只好寄情各種版本書目,並順道讀讀中外古今的藏書提要、書話文集,聊備飲鴆止渴之娛——周作人嘗曰:「看看書目雖不能當屠門大嚼,也可以算是翻食單吧。」依此類推,讀書話文章就彷彿進伙房觀廚師施展手藝了。漢芙、紐頓和其他許多人的著作,便是在那樣的環境條件下囫圇吞入肚的。
「藏書」在中國從來不是新鮮物事,「書話」在中文世界自有極其悠久輝煌傳統,光是近代名家,較合乎規格(述說蒐訪梗概、旁論版本源流、兼談掌故逸聞)的,稍早有黃丕烈、繆荃孫、葉昌熾、傅增湘、葉德輝、雷夢水……;晚近則有周越然、周作人、鄭振鐸、葉靈鳳、唐弢、黃裳……;今日尚可見的馮亦代、姜德明、黃俊東、董橋、彭歌……;而此時此地的隱地、舒國治、吳興文、鍾芳玲、傅月庵……等人的文章亦各存機妙;更甭提每位寫作者在其筆耕生涯中,皆不免或多或少沾帶過此類文章幾回。既有那麼多優秀的中文著作,或許正是無須假以外求的部分原因。
不過近年以來,連本土書話也迅速式微,原因很多也很明顯。但我認為:與其奢盼大家多讀、多買、多翻譯、多出版外國書話,倒不如設法提倡本土書話的產能、流通量。或者有人喟嘆今非昔比:古舊籍冊數量日稀;大量機械複製的印刷品早已泯滅版本差異;而目下出版物文質俱劣云云。話說回來,誰說買新書就肯定生不出有意思的書話來著?或許正因舊書日益難尋,反倒相對提高了鑽故紙的樂趣和挑戰性哩。眷戀舊書的人最易罹患這種「萬事莫如昨日好」的愁緒,我建議大家不妨以明天的眼光觀今日之書市,好好地淘書、買書、讀書、護惜書。如此一來,在這方既熱且潮、又窄又吵的海島上,「藏書」一途庶幾始能粗具樂趣。
就這一層意義來看,於此時此地千里迢迢地重新翻譯、出版這部上了年紀的外國書,不是稍嫌太鹵莽、唐突了嗎?這倒也不盡然。紐頓的書話文章當年曾適時開展了西方書話的另一番氣象,以《藏書之樂》作為藏書書寫的一個粗略斷代,前人的作品泰半出自學者、作家或書賈之手,內容偏重校讎、鑒賞、評價等功能,總與普通讀者隔著一大段距離。身為一名另有day job的藏書家,紐頓本人對「藏書」此一行當的理解和目光並不侷限於其光鮮、孤高的一面(由《藏書之樂》副題中的“kindred affections”亦可作「連帶併發的同類症狀」解,即可看出紐頓的慧黠與淘氣),他不揣己陋(其實他精得很)屢屢在文章中自曝、自嘲藏書家種種拙態洋相;讀過他的文章,大家才恍然自覺人人亦皆可成為一名common collector;書話一體開始百家齊鳴,而各種藏書文集自此紛紛問世。我寄盼這個中譯本多少也能在咱們這兒再扮演一次它當年的角色。
翻譯紐頓的文章,除了對自己的語文能力和文史知識造成相當程度的考驗之外;我在翻譯作業進行期間,雖然憑藉正當理由得以重溫這些雋永文章而又「度過許多愉快的夜晚」;但我本身其實是個傾向注視半截空水杯的人,對凡事總偏好以「負面表列」抱持最壞的看法;置身國事紛亂如麻、朝野吠鬥不休的囂譟島嶼,朝前看,雲深霧重、前途茫茫;往後瞧,坑坑疤疤、幾無建樹。值此時節,耽讀如此沁脾清肺的絕妙散文,從中親炙久遠前的文藝大家、紙上玩賞誘人的珍稀古籍,無寧是極度不切實際的奢侈行徑。我面對紐頓的文章,心底每每泛生這樣的踟躕。
但我想起一部成績平平卻頗能動人的老電影。由威廉.惠勒(William Wyler)執導的《忠勇之家》(Mrs. Miniver, 1942),影片描述英國一個中上階級家庭在戰前、戰時的日常生活之驟變與不移的處世情操,用以鼓舞當時仍深陷戰區的英國子民。我印象很深刻的兩場戲是:密尼佛家的長子小文(Vin)甫自牛津返鄉過節,年輕小伙子剛從高等學府學到許多新穎知識,對於自身所處的社會乃至整個世界,都萌生了嶄新的看法、議論。巧逢貴族後裔卡蘿(Carol)小姐登門造訪,大家閨秀應對進退一派得體,看在小文眼裡卻十足封建遺毒。滿腦子平權思想頓時化成一頓譏諷數落,得了理又不肯饒人,兩個小朋友一見面就鬧僵;事後小文回想卡蘿種種,益發覺得錯待千金,同時也按捺不住相思情愫,當晚親赴村里舞會場外守候(他古板得連舞會也不屑參加),並央人遞紙條將卡蘿喚出來,對自己先前的失態向小姐道歉。善良、溫婉又爽朗的卡蘿並未掛懷,仍大方地邀小文陪她一道回舞池。當時歐陸已是一片烽火,戰雲隨時籠罩英倫。一頭熱血正打算從軍報國的小文,即使花前月下仍忍不住問卡蘿:「說真格的,妳覺得現在是合適玩樂的時候嗎?」美麗的卡蘿小姐如此回答他:「難道你認為大家現在都該扳起臉孔?(Is this a time to lose one’s sense of humour?)」
是啊,幽默並非逃避,有真勇氣、具大智慧的人方能發揮幽默感(我指的當然是像紐頓先生、卡蘿小姐那種高級幽默;此間政客伶伎每天伶牙俐齒、嘻皮笑臉自非此屬),其實,幽默才是面對困境時最高明的態度。紐頓本人也經歷過經濟恐慌、第一次世界大戰、大蕭條等晦暗的時代,他卻始終抱持開闊的胸襟;倘若當時有人詰問紐頓:「還藏什麼書呢?現在頂要緊的就是拚經濟呀!」他一定也會說:「難不成,咱們都該扳著臉孔拚嘍?」。我們的社會之所以會搞得如此伊於胡底,令大家深感無可解脫的癥結,或許正是因為我們全都喪失了幽默感——不管是教訓別人的還是被別人教訓的都成天扳著臉。此時此地出版中譯版《藏書之樂》,或多或少也應該能點醒其他只會道貌岸然的人罷。
此次收入中文譯本的篇章,分別選自紐頓的五部同類著作,恰分為五卷都十九章。挑選的標準稍有參差,但約略以「較符合『藏書』旨趣」與「有特殊的文藝趣味」者為原則(唯一的例外是完全不涉及藏書的〈志願人人有,我的不算多!〉)。當然,未收錄的其他文章亦盡是字字珠璣逗趣、篇篇雋永可讀,惟考量篇幅有限,或其內容與今日此間讀者的距離更大,只有割愛遺珠一途。但我仍將五部書的完整目錄翔實列出,由讀者們自行一一睹目遐想。萬一「理直氣壯」的人夠多;加上這部中譯本意外撈得回本,那麼,其他諸如:臧否葛德溫行誼的〈荒唐哲學家〉、記述約翰生軼事的〈詹姆士.鮑斯威爾其人其書〉、〈高夫廣場幽魂未散〉、〈亦諧亦莊的約翰生詞典〉、緬懷城市餘暉的〈聖殿門今昔〉、〈風華絕代老倫敦〉、〈一八八○年代的倫敦〉、闡論英法國情民風差異的〈人比人果真氣死人?〉、剖析名家名作的〈奧斯卡.王爾德〉、〈華特.惠特曼〉、〈持平論布雷克〉……等光看標題就意趣橫生的文章,甚至紐頓的其他幾部著作:關於旅遊的嘻笑之作《糊塗旅行家》(A Tourist in Spite of Himself, 1930)、寓學問於閒散的《賽馬日,漫遊散錄》(Derby Day, and Other Adventures, 1934)、收錄三篇專題演講稿的《版本學與偽版本學》(Bibliography and Pseudo-Bibliography, 1936)……終有一天也都有機會以方塊字重新出土面世亦未可知。此外,書末的幾篇附錄來自我手邊碰巧擁有的幾份資料,托中譯紐頓得道之福一併昇天,我會在各附錄文前分別稍作簡短說明。
最後附帶一提:為數甚多的人耽溺淘書逸樂、藏書雅趣並不足為奇,但最能切膚知曉藏書甘苦冷暖的人或許未必是藏書家本人;而往往是他(或她)的身邊伴侶。放眼古今中外,如李清照、趙明誠:一旦搜得佳帖善本,兩人便蹭在一塊兒「校勘整集簽題……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而率」;或像法地曼伉儷3、戈爾德史東夫婦4那樣:鶼鰈倘佯於浩瀚書海;在典籍世界中分享精美、共體蹎躓,此等境界恐怕是所有愛書人之無上烏托邦。不幸地,我們較常看到的例子往往是:某一造戀書成癡、積冊無度;另一造則不勝其擾之餘,還得連帶蒙受其kindred affections。藏書誠有樂,禍害尤其多,犖犖大者包括:龐大的藏書量所造成的環境低劣、空間窄縮;終日耽讀導致四體不勤、目光短狹、食不知味……和——最教人忿恨難消的——另一半(或稱the worse half)的冷落怠慢。
翻開《藏書之樂》,紐頓的窩心獻辭傾刻映入眼簾(紐頓書中不時出現的紐頓夫人身影亦頗令人莞爾玩味)5;而我頻頻在此類著作中讀到作者或感激、或歌頌、或憐憫無辜的另一半(the better half)的題獻辭;除了紐頓之外,威廉.哈里斯.阿諾德6、約翰.卡特7、尼可拉斯.A.巴斯班斯8……一干人等(怎麼搞的全是男人?)全幹過這種得了便宜還賣乖的勾當。
遵循此項優良傳統,我似乎宜將此回譯作獻給我的妻子。雖然她在婚前對我的惡習早已略知一二,但是婚後十餘年,她眼見我變本加厲、毫無節制地購置、堆累書籍卻又疏於整頓,每逢中級地震,我們在自己的小公寓裡就能目擊走山、土石流;甚至當我為了實驗何種紙頁易受蟲害而走火入魔地學威廉.布雷德斯豢養蠹魚、白蟻9的時候,她也只能搖頭吁嘆所嫁非人。吾愛書籍;亦愛吾妻,我從未敢稍加思量兩者在我心目中的地位究竟孰輕誰重,只祈盼餘生永遠無須在書籍和她之間作唯一的痛苦選擇。她自然並非厭惡書籍(她自己的書也不算少,只是她既沒有又舊又破又髒的書,也從來不買「先買回家擱著,總有一天一定會讀」的書),而是比我更能感受大量書籍所帶來的實質禍害。
但我終究未敢剽學紐頓,為太太在「愛書人的天堂」預約一席之地——我堅持:當那一刻來臨,我的妻子值得晉身更清爽、整潔的境界。 二○○二年十月
1 〈一種溫文爾雅的瘋狂——讀海蓮.漢芙的《查令十字路84號》〉(《中國時報》2002.4.18)。
2 見《查令十字路84號》(時報文化出版)頁13。其實漢芙本人曾經上過紐約大學,只是在學期間不及年餘,校方即因經濟大恐慌而遣散學生。
3 Anne and George Fadiman,妻子是《愛書人的喜悅》(Ex Libris, Confessions of a Common Reader, 1998。中文版由劉建台翻譯,雙月書屋出版,一九九九年二月第一版)作者。
4 Nancy and Lawrence Goldstone,太太帶頭寫出《舊書與珍本——書海任遨遊》(Used and Rare, Travels in the Book World, 1997)、《略有破損——書林頻駐足》(Slightly Chipped, Footnotes in Booklore, 1999)、《窩心落款——新英格蘭偽書及其他書本故事》(Warmly Inscribed: The New England Forger and Other Book Tales, 2001)、《烈焰餘燼——一位大無畏學者的偉大事蹟,招致死罪的異端邪說,一部絕無僅有的珍本》(Out of the Flames: The Remarkable Story of a Fearless Scholar, a Fatal Heresy, and One of the Rarest Books in the World, 2002)。
5 美國波特蘭的鮑威爾書店(Powells Books)最近開價六百美元販售一部經過特別裝幀、紐頓親筆簽贈給他太太的首版《藏書之樂》,上頭的落款是:「致 令我生命如此快活並助我寫成此書的愛妻芭蓓特.E.紐頓。A.E.紐頓識於一九二○年六月十六日獲賓大頒贈學位之日。」(見第四頁附圖)
6 威廉.哈里斯.阿諾德(參見譯文第一卷第一章譯註72)在其著作《披荊斬棘話藏書》(Ventures in Book Collecting, 1923)中的題獻辭:「致吾妻」(TO MY WIFE)。
7 約翰.卡特(John Carter)在其著作《藏書之鑑賞及技巧》(Taste and Technique in Book Collecting, 1948)中的題獻辭也是:「致吾妻」(To My Wife)。
8 尼可拉斯.巴斯班斯(Nicholas A. Basbanes)在其著作《一任瘋雅——愛書家、藏書癖與無怨無悔的執迷》(A Gentle Madness: Bibliophiles, Bibliomanes, and the Eternal Passion for Books, 1995)中的題獻辭:「獻給康絲坦.V.巴斯班斯」(For Constance V. Basbanes)、在《堅忍卓絕——漫述書籍世界中的人、事、史、地》(Patience & Fortitude: A Roving Chronicle of Book People, Book Places, and Book Culture, 2001)中的題獻辭則是:「給CVB,且讓我倆攜手再共度二十五個年頭」(For CVB, and the next quarter-century)。
9 威廉.布雷德斯(參見譯文第四卷第二章譯註●)曾在《書的敵人》中提及某日收到書商特地為他保留的一尾肥碩書蟲,布雷德斯如獲至寶,雖然以上好的古版書頁殘片悉心餵食,但由於水土不符(布雷德斯自己推測),豢養三週後仍一命嗚呼。我養過不只一隻,也都沒能活過三個禮拜,想必它們一旦遠離書架,不能飽噬群書,便賭氣不碰嗟來之食也。此訓堪為每尾「生涯一緒論 在這個世界上,最有意思的東西就是「人」(「女人」自然也包括在內),其次便是「書」。藉由書籍,人們得以理解最深奧的秘密。雖然大多數人都說不出其所然或其所以然,但是任何一個曾經出書的人(如果他和出版商處得還不錯的話)只要花一點篇幅便可以說清楚書籍何以致之。
若干年前,有一位非常有學問的朋友出了一部書。他在前言中提醒「眾看倌」宜略過第一章不讀。言下之意,他似乎暗示大家(連我也信以為真):其餘章節均耐讀易懂,但事實卻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說穿了,那部書根本就不是打算要寫給「眾看倌」看;充其量只是一部出自學究之手、專供學究們研讀的書罷了。 如今,我卻反其道而行。我這部書乃專為那些在「勞碌營生」之餘,仍自許為熱愛閱讀的人(即:吾輩芸芸眾生之中為數何其多的族類)而寫。鑒於這是我破天荒的頭一部作品,謹容我在此談談它的來龍去脈。
一九一三年的某個秋日午後,我的某位好友(亦是我有幸共事多年的事業夥伴)談起我該找時間好好地休個假了,他還硬塞給我一冊《地理雜誌》(Geographical Magazine)。那一期的專題是「埃及」;於是,耐不住雜誌上眩目照片的誘惑,我當下便決定要給自己來一趟溯尼羅河之旅。
光陰似箭,也不過才隔了幾個禮拜光景,我的太太和我已經置身地中海,乘坐在一艘航向亞歷山卓的汽船上。我們剛停靠過熱那亞,不日即可抵達那卜勒斯。就在此時,一股思鄉之情悄悄襲上我的心頭。一想起我曾經在倫敦度過無比愉悅的假期,相形之下埃及頓時變得索然乏味。尼羅河源遠流長,數千年來滔滔不絕,未來想必亦將繼續奔流不輟;而倫敦等著我蒐探尋訪的書籍卻片刻不待人。我只好硬著頭皮向太座請示,一見她對我的臨時動議沒有表示強烈反對,我們便在那卜勒斯下船。先到羅馬的友人住處盤桓幾個禮拜,接著便「火速兼程」踏上前往倫敦的征途。
行文至此,讀者們一定也發覺了,我實在不夠格當旅人遊客。然而對於倫敦,我卻始終百遊不倦。倫敦處處可見深厚的文藝遺產、名勝史蹟——更別提街上櫛比鱗次的商店、逛不完的鋪子,陳列著我絲毫無心戀棧的各色各樣玩意兒;當然還有那些又髒又舊的書肆,裡頭擺滿了我覬覦的東西。 某個陰沉沉的日子,我在查令十字路上以一先令淘到一部理察.勒迦涅9的絕妙好書《英格蘭遊記》10。勒迦涅同我一樣德性,似乎也對旅行不甚在行——他鮮少抵達出發前原本設想好的目的地,途中不是迷了路就是臨時改變主意;一旦他在某間舒適的旅店落腳,草草吃過一頓飯、點起菸斗、翻開一本書,原定的行程便就此無疾告終。
我對旅行的想法正與他如出一轍!我上一回讀《匹克威克外傳》11正值我在義大利北部旅遊的期間。當小汽艇在義大利的湖光山色間流連穿梭時,我卻老是待在密不通風的吸菸艙裏手不釋卷。
正當我在倫敦忙著一間接一間逛店尋寶時,腦際突然閃過一個念頭:何不提筆寫點關於我那些藏書的文章呢?談談我於何時何地尋獲那些書、聊聊它們各自所費幾何、分別購自何人(其中大多是我熟識的人)之手……諸如此類的事兒。於是,一等假期結束,我回顧那段時日中令我開懷的點點滴滴,寫成一篇〈海外得書記〉;隨後又寫出〈海內得書記〉,我當初原本是打算將兩篇文章湊合起來,印成一冊我姑且稱之為《藏書之樂》的小書,分贈長年以來不斷給予我無限包容的諸位親朋好友12。一九一四年七月,大戰爆發前夕,我才剛把書稿送進印刷廠,沒隔幾天,歐洲就風雲變色了。如今,終戰之日仍遙遙無期,大家都惶惶不可終日。有那麼一陣子,任誰也沒有興致開卷展讀一部書。深感自己一時衝動幹了傻事,我終究還是識相地將稿子從印刷廠抽回來,擱在一旁,然後回首投入正常事務——即「勞碌營生」——之中。
拜倫嘗曰:「所有的塗塗寫寫,終究僅為博君一粲。」13這些年以來,我一直按捺不住這種「塗塗寫寫」的癮頭。這股感覺的強度與日俱增,而我也逐漸想通:就算是打仗,我們依然應該努力讓自己過正常日子;原有的生活規模畢竟還是得盡可能地維持該有的樣子。於是,出版那部小書的念頭又在我心中重新燃起。 朋友們屢屢建議我不妨將那幾篇文章投到《大西洋月刊》發表。我並不清楚他們和那份辦得有聲有色的雜誌之間究竟有什麼過節,但我實在經不起老把《大西洋》掛在嘴邊的一干人不斷慫恿。於是,當我某天又無意間瞥見那篇稿子,心裡頭便嘀咕:把稿子寄給編輯瞧瞧橫豎也花不了幾毛錢。那個時候,我甚至連《大西洋》的編輯是哪位仁兄都不曉得哩。所以,各位不難想像,當下面這封信寄達的時候,我高興成什麼德性了。
......(更多)
目录
......(更多)
读书文摘
一个人之所以要买某部书,最好也最明显的理由便是:他觉得买了会比没买开心。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