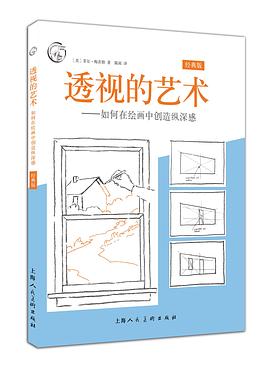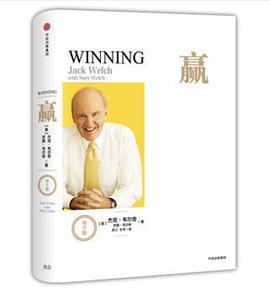内容简介
她以一支笔坚持看守个人文字上的简单和朴素
从遥远的撒哈拉到敦煌戈壁,她不随波逐流,也不诠释人生,只做生活的见证者
她是我们心中浪漫、洒脱、真性情的永远的三毛,永恒的传奇
《雨季不再来》收录了三毛17~22岁发表的作品。当三 毛还是二毛的时候,她是一个逆子,追求每一个年轻人自己也说不清的那份情怀,用文字记录下思想上的迷惘与感伤。然而历经十年数不清的旅程,无尽的流浪和情感上的坎坷之后,她终于醒悟到了这一段日子并非虚度,而是让她成为了一个对凡事有爱、有信、有望的三毛,造就了她的浪漫与真性情。那交错着甜蜜伤感少年心事的雨季虽然漫长,却总有一日,可以穿着干燥的黄球鞋踏上充满阳光的大道。
......(更多)
作者简介
三毛(1943~1991),本名陈懋平,因为学不会写“懋”字,就自己改名为陈平。旅行和读书是她生命中的两颗一级星,快乐与疼痛都夹杂其中,而写作之初纯粹是为了让父母开心。她踏上广袤的撒哈拉,追寻前世的乡愁,和荷西在沙漠结婚,从此写出一系列风靡无数读者的散文作品,把大漠的狂野温柔和活力四射的婚姻生活,淋漓尽致展现在大家面前,“三毛热”迅速从台港横扫整个华文世界。然而荷西的突然离世,让她差点要放弃生命,直到去了一趟中南美旅游,才终于重新提笔写作。接着她尝试写剧本、填歌词,每次出手必定撼动人心。直到有一天,她又像儿时那样不按常理出牌,流浪到了遥远的天国。
......(更多)
目录
当三毛还是在二毛的时候
胆小鬼
吹兵
匪兵甲和匪兵乙
约会
一生的爱
紫衣
蝴蝶的颜色
逃学为读书
惑
蓦然回首
惊梦三十年
我的三位老师
得奖的心情
补考定终生
月河
极乐鸟
雨季不再来
一个星期一的早晨
秋恋
西风不识相
安东尼•我的安东尼
初见蒙娜丽莎
最快乐的教室
倾城
还给谁
老兄,我醒着
赴欧旅途见闻录
我从台湾起飞
翻船人看黄鹤楼
去年的冬天
书信(西班牙•台湾)
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日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日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更多)
读书文摘
我常常想,命运的悲剧,不如说是个性的悲剧。我们要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固执不变当然是可贵,而有时向生活中另找乐趣,亦是不可缺少的努力和目标;如何才叫做健康的生活,在我就是不断地融合自己到我所能达到的境界中去。
流去的种种,化为一群一群蝴蝶,虽然早已明白了,世上的生命,大半朝生暮死,而蝴蝶也是朝生暮死的东西,可是依然为着它的色彩炫目神迷,觉着生命所有的神秘与极美已在蜕变中彰显了全部的答案。
姐姐是温驯又孝顺的,她穿上与我一模一样的新衣,不断的拿一面小镜子照自己。我偷看那件衣服,实在也是不太难看,心里虽然比较泰然,可是不肯去试它。
我们家没有信箱,一向从竹子编的篱笆洞里传递着信件。每当邮件来的日子,就会听见喊:“有信呀!”于是总有人会跑出去接的。那是多年前的往事了。当年,我的母亲才是一个三十五、六岁的妇人。她来台湾的时候不过二十九岁。
由舒兰街到爱国西路是一段长路。母亲和姐姐的身上还放着两个大锅,里面满盛着红烧肉和另一锅罗宋汤,是母亲特别做了带去给同学们吃的。前一天夜里,为了这两样菜,母亲偷偷的做了很久都没进房睡觉。
那时候,我乘过十二路公共汽车,还有三轮车。上学是用走路的。每年一度的旅行也是全年级走路,叫做——远足,是不坐车的。星期天我照例要去学校,姐姐在二女中,她可以放假。母亲说,那日仍然要去补习,到了下午两点正,她会带了姐姐和新衣服来学校,向老师请假,等我换下制服,就可以去了。
姐姐告诉我,母亲的同学嫁的都是有钱人,那天去开同学会,我们小孩子会有冰淇淋吃。在那以前,吃过冰棒、仙草冰、爱玉冰,可是没有吃过真的冰淇淋。姐姐说,在大陆我们家每年夏日都吃那东西的。我总不能有记忆。
于是才突然发现原来妈妈也有同学,那么她必然是上过学的咯!后来就问母亲,问念过什么书。说高中毕业就结了婚。看过《红楼梦》、《水浒传》、《七侠五义》、《傲慢与偏见》、《咆哮山庄》……在学校母亲打篮球校队,打的是后卫。听见母亲说这些话,看过我也正开始在看的书,禁不住深深的看了她一眼,觉得这些事情从她口里讲出来那么不真实。生活中的母亲跟小说和篮球一点关系也没有,她是大家庭里一个不太能说话的无用女子而已。在那个家里,大伯母比母亲权威多了。我真怕的人是大伯母。
到了晚上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小孩子照例打地铺睡在榻榻米上,听见母亲跟父亲说:“要开同学会,再过十天要出去一个下午。两个大的一起带去,宝宝和毛毛留在家,这次我一定要参加。”父亲没有说什么,母亲又说:“只去四五个钟头,毛毛找不到我会哭的,你带他好不好?”
台北市在当年的一个星期天,那样的模糊和空虚。
“走啦!开走啦!”我喊着。母亲哗一下子将全部挡雨的油布都拉掉了,双眼直直的看住那辆车子——那辆慢慢往前开去的车。“老周——去追——。”我用手去打老周的背,那个好车夫狂冲起来。雨水,不讲一点情面的往我们身上倾倒下来,母亲的半身没有坐在车垫上,好似要跑似的往前倾,双手牢牢的还捧住那锅汤。那辆汽车又远了一点,这时候,突然听见母亲狂喊起来,在风雨里发疯也似的放声狂叫“——魏东玉——严明霞、胡慧杰呀——等等我——是进兰——缪进兰呀——等等呀——等等——。”雨那么重的罩住了天地,母亲的喊叫之外,老周和姐姐也加入了狂喊。他们一直叫、一直追,盯住前面那辆渐行渐远的车子不肯舍弃。我不会放声,紧紧拉住已经落到膝盖下面去的那块油布。雨里面,母亲不停的狂喊使我害怕得快要哭了出来。呀——妈妈疯了。
好不容易那一排排樟树在倾盆大雨里出现了,母亲手里捏住一个地址,拉开雨篷跟老周叫来叫去。我的眼睛快,在那路的尽头,看见一辆圆圆胖胖的草绿色大军车,许多大人和小孩撑着伞在上车。“在那边——”我向老周喊过去。老周加速的在雨里冲,而那辆汽车,眼看没有人再上,眼看它喷出一阵黑烟,竟然缓缓的开动了。
“这种配法是死——人——色!”我说。“妹妹,妈妈没有其他的布,真的!请你不要伤心,以后等妈妈有钱了,一定给你别的颜色衣服……。”母亲一面说一面拿起新衣要给我套上试试看,我将手去一挡,沉着脸说:“不要来烦!还有算术要做呢!”母亲僵立了好一会儿,才把衣服慢慢的搁在椅背上。
母亲心不在焉的淡然,听着听着,突然说:“天明和天白咳嗽太久了,不知好了没有——。”她顺手拿起电话,按了小弟家的号码,听见对方来接,就说:“小明,我是阿娘(注:祖母)。你还发不发烧?咳不咳?乖不乖?有没有去上学?阿娘知道你生病,好心疼好心疼……”
许多年过去了,上星期吧,我跟母亲坐在黄昏里,问她记不记得那场同学会,她说没有印象。我想再跟她讲,跟她讲讲那第一件新衣,讲当年她那年轻的容颜,讲日本房子窗外的紫薇花、眼神、小弟、还有同学的名字。
总之,信交给母亲的时候,感觉到纸上写的必是一件不同凡响的大事。母亲看完了信很久很久之后,都望着窗外发呆。她脸上的那种神情十分遥远,好像不是平日那个洗衣、煮饭的妈妈了。在我念小学的时候,居住的是一所日本房子,小小的平房中住了十几口人。那时大伯父母还有四位堂兄加上我们二房的六个人都住在一起。记忆中的母亲是一个永远只可能在厨房才会找到的女人。小时候,我的母亲相当沉默,不是现在这样子的。她也很少笑。
为了那次的出门,母亲低着眼光跟大伯母讲过一两次,大伯母一次也没有搭理。这些事情,我都给暗暗看到眼里去。这一回,母亲相当坚持。等待是快乐又缓慢的,起码母亲感觉那样。那一阵,她常讲中学时代的生活给我们听,又数出好多个同学的姓名来。说结婚以后就去了重庆,抗战胜利又来到了台湾,这些好同学已经失散十多年了。说时窗外的紫薇花微微晃动,我们四个小孩都在属于二房的一个房间里玩耍,而母亲的眼神越出了我们,盯住那棵花树又非常遥远起来。
到了家,母亲立即去煤球炉上烧洗澡水,我们仍然穿着湿透的衣服。在等水滚的时候,干的制服又递了过来,母亲说:“快换上了,免得着凉。”那时她也很快的换上了居家衣服,一把抱起小弟就去冲牛奶了。
母亲的同学会订在一个星期天的午后,说有一个同学的先生在公家机关做主管,借了一辆军用大车,我们先到爱国西路一个人家去集合,然后再乘那辆大汽车一同去碧潭。
母亲倒身在三轮车上。老周跨下车来,用大手拂了一下脸上的雨,将油布一个环一个环的替我们扣上。扣到车内已经一片昏暗,才问:“陈太太,我们回去?”母亲嗳了一声,就没有再说任何话。车到中途,母亲打开皮包,拿出手绢替姐姐和我擦擦脸,她忘了自己脸上的雨水。
母亲收到同学会举办的郊游活动通知单之后,好似快活了一些,平日话也多了,还翻出珍藏的有限几张照片给我们小孩子看,指着一群穿着短襟白上衣、黑褶裙子的中古女人装扮的同学群,说里面的一个就是十八岁时的她。
其中一张小照,三个女子坐在高高的水塔上,母亲的裙子被风卷起了一角,头发也往同一个方向飘扬着。看着那张泛黄的照片,又看见地上爬着在啃小鞋子的弟弟,我的心里升起一阵混乱和不明白,就跑掉了。
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眼睁睁的巴望母亲不再裁报纸,拿真的布料出来给人看。当我有一天深夜放学回来,发觉母亲居然在缝一件白色的衣裳时,我冲上去,拉住布料叫了起来:“怎么是白的?!怎么是一块白布?!”丢下书包瞪了不说话的人一眼,就哭了。灯下的母亲,做错了事情般的仍然低着头——她明明知道我要的是粉蓝色。
从母亲要去碧潭参加同学会开始,那许多个夜晚补习回家,总看见她弯腰趴在榻榻米上不时哄着小弟,又用报纸比着我们的制服剪剪裁裁。有时叫姐姐和我到面前去站好,将那报纸比在身上看来看去。我问她,到底在做什么?母亲微笑着说——给你和姐姐裁新衣服呀!那好多天,母亲总是工作到很晚。对于新衣服这件事情,实在是兴奋的。小学以来,每天穿的就是制服,另外一件灰蓝条子的毛线背心是姐姐穿不了轮到我穿,我穿不了又轮大弟穿的东西,它在家里是那么的永恒不灭。直到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向母亲讨,想留下背心做纪念。而当时,是深恶它的。
同学会那个清晨,我很早就起来了,趁着大人在弄稀饭,一下就把自己套进了那件并不太中意的新衣服里面去。当母亲发觉我打算不上学校,就上来剥衣服。我仍是被逼换上制服背着书包走了。姐姐陪我一路走到校门口,讲好不失信,下午两点钟会来接,一定会来接的。我不放心的看了姐姐一眼,她一直对我微笑又点头。中午吃便当的时候天色开始阴沉,接着飘起了小雨。等到两点钟,等到上课钟又响过好一会,才见母亲拿着一把黑伞匆匆忙忙由教务处那个方向的长廊上半跑的过来。姐姐穿着新衣服一跳一蹦的在前在后跟。
第二天放学回来,发觉白色的连衣裙已经缝好了,只是裙子上多了一圈紫色的荷叶边。
雨,越下越大,老周浑身是水,弯着身体半蹲式的用力踩车,母亲不时将雨篷拉开,向老周说对不起,又急着一下看表,一下又看表。姐姐很专心的护汤,当她看见大锅内的汤浸到外面包札的白布上来时,就要哭了一般,说妈妈唯一的好旗袍快要弄脏了。等到我们看见一女中的屋顶时,母亲再看了一下表,很快的说:“小妹,赶快祷告!时间已经过了。快跟妈妈一起祷告!叫车子不要准时开。快!耶稣基督、天上的父……。”我们马上闭上了眼睛,不停的在心里喊天喊地,拼命的哀求,只望爱国西路快快出现在眼前。
很快被带离了教室,带到学校的传达室里去换衣服。制服和书包被三轮车夫,叫做老周的接了过去,放在坐垫下面一个凹进去的地方。母亲替我梳梳头发,很快的在短发上札了一圈淡紫色的丝带,又拿出平日不穿的白皮鞋和一双新袜子弯腰给我换上。母亲穿着一件旗袍,暗紫色的,鞋是白高跟鞋——前面开着一个露趾的小洞。一丝陌生的香味,由她身上传来,我猜那是居家时绝对不可以去碰的深蓝色小瓶子——说是“夜巴黎”香水的那种东西使她有味道起来的。看得出,母亲今天很不同。老周不是我们私人家的,他是在家巷子口排班等客人的三轮车夫,是很熟的人。我和姐姐在微雨中被领上了车,位置狭窄,我挤在中间一个三角地带。雨篷拉上了,母亲怕我的膝盖会湿,一直用手轻轻顶着那块黑漆漆的油布。我们的心情并不因为天雨而低落。
我穿上旧制服,将湿衣丢到一个盆里去。突然发现,那圈荷叶边的深紫竟然已经开始褪色,沿着白布,在裙子边缘化成了一滩一滩朦胧的水渍。
怎么记得是我拿的信也很清楚:那天光复节,因为学校要小学生去游行,所以没有叫去补习。上午在街上喊口号、唱歌,出了一身汗便给回家了。至于光复节邮差先生为何仍得送信这回事,就不明白了。
总有一日,我要在一个充满阳光的早晨醒来,那时我要躺在床上,静静的听听窗外如洗的鸟声,那是多么安适而又快乐的一种苏醒。到时候,我早晨起来,对着镜子,我会再度看见阳光驻留在我的脸上,我会一遍遍的告诉自己,雨季过了,雨季将不再来,我会觉得,在那一日早晨,当我出门的时候,我会穿着那双清洁干燥的 黄球鞋,踏上一条充满日光的大道,那时候,我会说,看这阳光,雨季将不再来。
人之所以悲哀,是因为我们留不住岁月,更无法不承认,青春,有一日是要这样自然地消失过去。 而人之可贵,也在于我们因着时光环境的改变,在生活上得到长进。岁月的流逝固然是无可奈何,而人的渐渐蜕变,却又脱不出时光的力量。
真正的快乐,不是狂喜,亦不是苦痛,在我很主观的来说,它是细水长流,碧海无波,在芸芸众生里做一个普通的人,享受生命一刹间的喜悦,那么我们即使不死,也在天堂里了。
我唯一锲而不舍,愿意以自己的生命去努力的,只不过是保守我个人的心怀意念,在我有生之日,做一个真诚的人,不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执着,在有限的时空里,过无限广大的日子。
真正的快乐,不是狂喜,亦不是苦痛,在我很主观的来说,它是细水长流, 碧海无波,在芸芸众生里做一个普通的人,享受生命一刹间的喜悦,那么我们即 使不死,也在天堂里了。
人之所以悲哀,是因为我们留不住岁月,更无法不承认,青春,有一日是要这么自然的消失过去。 而人之可贵,也在于我们因着时光环境的改变,在生活上得到长进。岁月的流失固然是无可奈何,而人的逐渐蜕变,却又脱不出时光的力量。
有时候,我多么希望能有一双睿智的眼睛能够看穿我,能够明白了解我的一切,包括所有的斑斓和荒芜。那双眼眸能够穿透我的最为本质的灵魂,直抵我心灵深处那个真实的自己,她的话语能解决我所有的迷惑,或是对我的所作所为能有一针见血的评价。
......(更多)